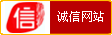道德经注解(1)
作者:辛一山
道德经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书籍,其地位不逊于易经。古代就有四个帝王专门为之做出注解,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道德经的知识性和重要性。在国外,老子《道德经》的影响也显而易见,黑格尔的辩证法、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现代物理的“宇宙爆炸论”都可见道德经影响的痕迹。现今存在的各种版本对道德经的注解。可以说有成千上万,本人仅就自己的理解对道德经做出注解。
要理解道德经必须了解道德经的整体性,道德经论述的是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规律,它是一种系统论。道德经的常用的说明手法是:用相反的两极对比方法来说明食物的发展规律和道理。古代的文章没有断句,因此对道德经的理解在古代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歧见。战国的韩非子和文子,以及汉朝的张道陵对某些相同的字句就有了非常不同的理解。因此,本版本的注解首先从断句开始,然后用系统论的观点进行前后对比,力求对道德经进行逻辑一致的解释。了解道德经还需保持中文的特点,那就是意会。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熟读《道德经》会有不同的理解。张道陵从道德经看到养生的道理;帝王从道德经里看到治国用兵的道理;伦理学家从道德经里看到道德教化的资本原理……
《老子》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原意是道路,这里喻指客观发展规律,或曰真理。可以理解为在思想的荒漠上的道路。
“道可道,非常道”的含义有两层,一.没有绝对真理,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现在认为是真理的以后不一定还是真理。二.真理是语言难以穷尽的,认为真确的真理描述都难以完整描述真理。
名:是事物的名称、外观、形状等。
今文:能说出来的真理不是经久不变的真理,真理是随着事物的变化发展而发展的;真理的描述必定有瑕疵,非常道是没有恒道,不是绝对真理。可以描述或存在的事物,不能长期的保存自有的形态和性质。如岩石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成为砂石、尘土。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天地产生的初始是混沌状态,这时什么都没有名称。万物产生后,人为了分别才有了它们各自的名称。因此有名是分辨万物的基础。
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恒无,欲以观其妙”以无的观点,即从初始状态出发,是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恒有,欲以观其徼”,(第十一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以从事物存在的状态和实际的发展情况来考察事物发展波及的边界和影响。
玄:原意为黑色,事物为黑色则难以观察到边界和形状。这里引申为难以描述和理解。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有和无的概念有相同的出处,但名称不一样。它们都产生于事物发展的初始。无:着重于初始状态,有:是人类为了分辨万物而产生的观念。有和无这两个概念都是属于难以理解的概念。有和无的相互演化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关键,也是探究世界的发展的方法。
本章难点:是对玄的解读,玄之又玄即有无的相互变化。
《老子》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斯:放句前为代词,是“这”的意思;放句后为语气词,意为“尽”。美:是人的一种意识,产生于人的感应,是一种意识共鸣。斯断句为后是因为,“恶”与“不善”已是确定的主语,加上斯过分强调与老子的描述手法和语气不符。“皆”是理解本句的关键。
天下人都知道美的事物为什么是美的道理,那么被人厌恶、嫌弃的事物就难出现。天下人都知道什么行为和品质是好的行为品质,而且好的行为品质对于个人是有好处的时候,那么不良的行为和品质就难以出现。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恒也:就是常理,是普遍规律。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因此圣人处世以“无为”为原则,无是万物的初始,也就是说要处理研究事物必须从事物的发端开始。如要教化人民,必须先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说不用语言来教导人而是以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来教化人。
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万事万物周而复始,难以找到开端;赖以生存的决定性因素难以被观察考虑到(如阳光);维持生存的因素并居功,自恃;如(空气);这些都是基本的因素,人们虽没有意识到阳光和空气是生存的必需品,但动植物都需要阳光。
本章的要义是讲教化,要求要以身教来推行教化,一切教化从初始开始(无为)。领导人从自己的行动开始进行教化,比进行宣传和实施各种规定都管用。
《老子》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不推崇英雄、贤人,使人民不争名利;不让稀罕难得的物品有昂贵的价格,可以防止出现盗贼;不出现欲望可实现的机会或路径,民众的心就不会乱。
“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因此,高明的治理方法是让人民有宽容的心,让人民不遭受饥饿。让人民没有强烈的欲求,让人民体格健壮。保持让人民处于不分辨贤愚、贵贱,也保持让民众没有强烈欲望。使得那些智力稍高的的人无法利用比别人高的智慧获利,不敢随意投机取巧。这样的原始状态的治理方法,也就是从初始阶段解决问题的“无为”方法。那就没有什么治理不了的。
本章的要义是不能让社会出现太大的分化,这样社会就不会有大贫富分化,也不会有太强烈的私人欲望,大家能够有平等机会,这样的社会就会和谐,容易治理。
《道德经》注解(2)
《老子》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也;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用本义时读yù)有人,有的——泛指人或事物。
道,冲而用之,
道的原理是“冲而用之”,这与惯常的道德经解释是非常不同的。江湖术士因为对道的误解而解读阴阳、八字,把冲理解为克,因此衍化出很多什么劫煞、刑冲的概念。而实际的用道原理贵在“冲”,这就是矛盾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体,有冲才能用道。
或不盈也;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道不会盈满,它象深渊可包含万物,道应该是万物的根源。道的功效可折挫锋锐;可解除纷争;可和合、消弭光线;可依附弱小而不显其强大功能。它非常的深远,难以观察,但又确实存在。我都不知道这“道”是谁的后代,它应该比所有可观察到的物质现象还要早出现。
本章讲道的运用,及道的功能。
《老子》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tuó)龠(yuè)与虚而不淈(gǔ)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自然生成,大家看不到天地的仁义,因为对天地来讲,万物都是象用草扎的祭祀品一样,没有分别。圣人在我们平常人看来也看不出他们的仁义,因为他们对待民众不分彼此,一视同仁。这原理就象天地对待万物不分彼此一样。
天地之间,其犹橐(tuó)龠(yuè)与,虚而不淈(gǔ),动而愈出。
橐 tuó 口袋:负书担橐。 〔橐驼〕即“骆驼”。 古代的一种鼓风吹火器:“具炉橐,橐以牛皮”。
龠 yuè 古代乐器,形状像笛。淈:gǔ 搅浑
天与地之间,好像是装书的皮口袋,也象是吹奏的乐器。它虚空难以观察,但难以搅浑;它象乐器,吹动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古代人难以理解,现代人知道空气的本质后就容易理解这层意思了)
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这句话很难理解,要引用老子的学生文子《玄通真经》来加以解释。“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夫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空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垠,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听到或者见到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会影响对于事物道理(数,引申为原理)理解。所谓数穷是表示难以理解事物道理。因为先入为主,有了爱憎,则有了立场,因此有成见,因此而不能客观的观察理解事物。理解事物最好的方法就是“守中”,也就是说没有立场和偏见。
本章以客观世界的现象来说明 “道”的原理,以及观察和认识“道”的方法,那就是不要有成见和立场才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老子》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pìn)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兮其若存用之不勤。
牝:丘陵为牡,溪谷为牝。谷:两山间的夹道或流水道,或指两山之间:山谷。河谷;庄稼和粮食的总称:五谷,百谷。
“谷者,欲也。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牝者,地也。体性安,女像之,故不掔。男欲结精,心当像地似女,勿为事先。“玄牡门,天地根。”牝,地也,女像之。阴孔为门,死生之官也,最要故名根。男荼亦名根。“绵绵若存。”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年以知命,当名自止。年少之时,虽有当闲省之。绵绵者,微也。从其微少,若少年则长存矣。今此乃为大害。道造之何?道重继祠,种类不绝。欲令合精产生,故教之年少微省不绝,不教之勤力也。勤力之计,出愚人之心耳,岂可怨道乎!上德之人,志操坚彊,能不恋结产生,少时便绝,又善神早成。言此者,道精也,故令天地无祠,龙无子,仙人无妻,玉女无夫,其大信也。“用之不勤。”能用此道,应得仙寿,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老子想尔注)。
这里考虑到牝和谷的含义,“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应正解为:宽容接纳的精神是难以觉察的“玄牝”。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兮其若存,用之不勤。宽容接纳的方法是天地衍化的根本,它可以让事物发展绵绵不绝,却又难以察觉。照这样的方法运用就可以事半功倍。
本章要义是: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是阴阳演化,阴孕育万物,因此立事的根本要有谷一样的情怀,要宽容接纳。这也是我们中国历经磨难而可以长存的法宝。
《道德经》注解(3)
《老子》第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天地自己不生长,因此能够长久生存。(不生者无寿命限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也是中国养生的重要法宝。)
因此,圣人退自身不争先,而身先;不考虑自身的存在和生存问题,但因为是领袖能够代表大众而获得保护而存在。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因为圣人们无私,而是因为他们代表大众利益,因此在有危险时他们获得优先保护,而在实际的个体存在上体现为优先获得保护。
本章要义:提倡大公无私,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和生存的人往往因为能够代表大众利益而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中国道德建构的重要基础。
《老子》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最好的的行为和品质象水。水有利于万物,而不与其他的事物争功利。它处于众事物嫌弃的地方(如下水道),因此水的品质类似于“道”。居住在适宜的地方;与人相处善用仁慈;言语有信用;施政合适,不虐民;遇事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行动时会把握最佳时机;这些都是类似道的好品质和行为。因为为人处事不与别人争,因此不会有什么祸端和烦恼。
本章要义是宣扬帮助人而不彰显,不彰显和不争的态度是消灭祸端的根本。中国古语云:“福莫大于无祸”。
《老子》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持杯子装水,不如将杯子固定再装水多。揣摩别人的心思而投机巧,则难以长期有效和获利,有时甚至要危害到自己。满堂的金银财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长期不丢失。富贵了还要骄纵,就违反了物极必反的原理,这是自讨苦吃,早晚报应。功遂身退,不居功自傲是符合天道的。
本章要义是讲明物极必反的原理,什么事都要有度,不要过分。极力要做得最好,往往难以达致目标。就像往水杯装水的原理一样,自然的固定放置可以比手拿着装更多的水。
《老子》第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搏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监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天门开阖(hé)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以为乎生之畜也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魄:人生始化曰魄,既生曰魂。魄则阴虚,魂则阳满,言人载虚魄,常须营护复阳。阳气充魄则为魂,魂能运动,则生全矣。一者,不杂也。复阳全生,不可染杂,故令抱守淳一,能无离身乎?(唐玄宗注解道德经)
老子将人的身体当作是运动的营房,载:装载、记载是存放记录的意思,营是驻地营房;。抱一:是合一,有修习道教原理的人容易理解。
身体犹如移动的营房,里面存载着人初生的精神,要坚持使之与人的身体一致,不要让这样的生存本原离开身体。意指人自然的生存指向和状态,要坚守。顺其自然。
搏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监,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
调养气息,疏通经络可以让人的身体如婴儿般柔软。
监:察也,古通鉴。玄监意指难以描述的分辨能力,意指意识。
去除意识,不要存在杂念,就可达致身心合一。爱民治国也一样要顺其自然,不能以机巧、智谋来治理。
天门开阖(hé),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以为乎?生之,畜也。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
天门在养生学来讲是人的百会穴,也有指口鼻呼吸器官的。
百会穴开合要象女人一样,才可以顺利获取天地精气。百会进入的精气要想象成如光线一样的贯通经脉,让它们自然到达,不要有太强的意识指挥。生的原理是蓄养。道的原理是帮助生存而人们觉察不到(如阳光空气),即使是正在起作用帮助人也不要居功。帮助生长而不损害别人的发展趋势,就是最高的道德。
本章要义:老子用养生学的原理来说明说其自然的重要性。人是最复杂的系统,可是说其自然就可以长寿、健康。爱民治国的原理也一样,它们不会比人的生理系统和过程更复杂。处理复杂的事物要用简单地方法,那就是“顺其自然”。在这一章里老子记载下我国最早心里学研究的文字记录:涤除玄监,能无疵乎。养生的气功无杂念和无意识是提高功力的关键。
《道德经》注解(4)
《老子》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gǔ),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yán)埴(zhí)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yǒu)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毂:车轮中心,有洞可以插轴
的部分,借指车轮或车。埏:用水和(hu?)土。埴:黏土。牖:窗户
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起组成了车轮,由车轮和其他的构件组成了车子,大家只知道车的存在而没意识到组成车轮的条幅和车轮的存在。那是因为各种构件都成为体现车子功能的组成部分。将粘土和水做成瓷器,大家也意识不到粘土和水的存在,那也是因为它们成为体现瓷器新功能的组成部分。一个房屋要开门和凿窗,可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单独存在,那是因为它们成为了房屋总体功能的组成部分。因此“有”是大家意识到的好处,而“无”是组成体现总体好处的各种功能。
本章要义:利用的词组由此而来。“无” 有大的的用处,各种各样的大好处和利益是由细小的好处,也即“无”构成,因此老子提倡“无为”。这章节还可以理解到有无的相互变化,对车轮来讲条幅是无,车轮是有,对车子来说,车子是有而车轮是无。
《老子》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tián)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丰盛的食物,使人舌不知味;纵情狩猎,使人心情放荡发狂;稀有的物品,使人行为不轨。因此,圣人但求吃饱肚子而不追逐声色之娱。所以摒弃物欲的诱惑而保持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
本章要义:为腹不为目,什么事都要抓住要点。人的生存重点是热量的维持和机能的维续,因此重要的是温饱问题。
《老子》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受到宠爱和受到侮辱都好像受到惊恐,把荣辱这样的大患看得与自身生命一样珍贵。什么叫做得宠和受辱都感到惊慌失措?得宠来自上级,得到宠爱感到格外惊喜,失去宠爱则令人惊慌不安。贪宠之人为下之人,为邀宠必受辱。这就叫做得宠和受辱都感到惊恐。什么叫做重视大患像重视自身生命一样?我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我有身体;如果我没有身体,我还会有什么祸患呢?因此,珍惜天下百姓犹如珍惜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人就可以将天下给他管理。爱惜天下百姓犹如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人就可以将天下交给他治理。
本章要义:宠辱都是因为利益,如果不那么刻意的追求利益,则不会有得失受惊的心态。受惊,心情不好是身体不健康重要诱因。要健康就不要有太多的物欲。圣人以身作则,感同身受。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才有可能作为统治者。不爱惜百姓,不了解民众疾苦的统治者难以长久。
《老子》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想看看不到的我们称为夷,想听听不到的我们称为希,想拿拿不起的我们称为微。夷、希、微这三个概念我们难以再进行仔细的考究和再定义。因为它们难以捉摸,因此它们混而为一,这就是道。它的上面不白,下部也不黑(难以名状)。道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但又说不出来。在事物发展终结时又再观察不到道了。所以,道的形状是没有形状,它没有一般物体那样的形状。我们把它称为恍惚,即有时看到有时看不到。我们迎着“道”看不见它的前面,跟随着“道”也看不见它的后面,这就是道。用古代的“道”来为处理现今的各类事物获得好处服务,我们就能够知道古代的圣人为什么可以轻松的治理天下。这就是道的规律。
本章要义是阐明和定义道,道是难以名状的,但道存在于事物发展的始终。道是世界的本原。老子对道的定义解决了西方哲学的难题,西方哲学的难题就是对于“一”的定义,也就是对于什么是世界的本原的定义。对“道”的定义是老子对全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道德经》注解(5)
《老子》第十五章
古代善于为道和用道者,微妙玄通,难以认识。因为难以认识,故强行将“道”的效用和功能进行解释和形容。行道者的行道原理犹如冬天涉水过河,快乐就像看见河面结冰可以方便过往;犹疑就像
说到浑浊的河水,那么再用浑浊的河水来做例子说明用道的原理。浑浊的河水怎么才可以清澈?只有使之静止,慢慢等待澄清;谁能够有长久的安稳生活?只有让生活系统的运动机制如植物生长般,循序渐进、周而复始,一切要顺其自然,才可以“安以久”。使用道的原理是不能够盈满,也就说不能过分。因为不盈满和过分,是以能够隐蔽不成为焦点和攻击目标,因此可一再的成功,没有阻力。
本章要义:前一章讲道的定义,这一章讲道的运用。用道的原理在于知己知彼,过河时虽然在冬天,但如果连河水干枯和汹涌时的状态都了然于胸,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预测的危险。用道不能盈满,要有充分的准备,也就是用三之一的力来处理事情,如果出现上面意外的情况则可以应付自如。这犹如炒股,很多专家教导用三分之一的资金进行一样,有大的意外就可以随时补仓或退出。
《老子》第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dǔ)。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虚和静是气功练习和修习佛法的窍门,老子用养生修道的道理来阐明事物发展的道理。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我们要观察它们周而复始的特性,也即规律性。众多的事物发展变化都可以寻找到它们的根源,找到根源守住生长变化的根本就可称为静。从根源再追寻发展路径就是复原发展轨迹;复原发展轨迹,找出周而复始的原理,这就是常理。我们知道事物发展的常理就叫做“明”。弄不明白事物的发展轨迹和原理的就叫做妄,妄是祸患失败的凶兆。知道事物发展常理的就有容量,可以容忍事物照本来的发展进程而进行,不会犯急躁冒进的毛病,不会“拔苗助长”。有容量有气度就可以有公正的态度,有公正的态度就有全面发展的系统观念,有全面发展的系统观念就是符合“天理”,符合天理就是照道的原理做事,依照道的原理做事就可以使事物发展顺利持久,也可以让人们的身心不受伤害。
本章要义:各代贵族注重养生,用贵族们常用的养生道理来说明道的功效。“复归其根”以及顺其自然是道的根本。这与后来四十八章的方法论“损之又损,及至于无”是一致的。
《老子》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注释:本章亦属难解的章节。有些将第一句里的下改为不。我们从老子想尔注的解说可以知道下还是正确的。唐玄宗等就将太上以
最早的时候,人们能够感知道的存在。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道”的原理,并愿意使用。再发展人们认识到“道”具有指导实践的功效,因此道成为赞赏和提倡学习的对象。再后来,人们只使用道的功能而忘却了道的原理,对于道就产生了畏惧。由于对道的认识逐渐的退化,人们开始不相信有“道”这样的规律,并有贬低、诋毁“道”的种种行为。
侮辱道的行为的出现是因为有些人投机取巧,使用奸谋。使用奸谋、投机取巧的人多了社会的相互信任就失去了。这样相互欺骗的情况出现后,社会关系就恶化,大家互相算计,社会也就没有上面诚信可言。对于道的原理则早已完全不关心。
相似的事情是,有这样可贵的言论:“成功了或者事物发展顺利,人们就相信”,众人大都以成败论英雄。如果都依照“道”的原理做事就可以成功。而成功的道理也简单,那就是顺其自然,这老百姓也可以总结出来。
本章的要义是分辨缺失的主语,不能将主语“道”理解为其他。
《道德经》注解(6)
《老子》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大道失去了才有讲究仁义的需要;(在有大道,大家都遵循道的原则相处,根本就无所谓仁义。人与人相互间的关系恶化了,才有要求仁义教化以及宣扬的需要)民众聪
明了有智慧了,就会产生一些投机取巧的人,各类虚伪诈骗的事会会出现,大家都以为可投机取巧。结果为了相互防备而失去了群体合作的力量。(这好像西方的逻辑学家推论人不能也没有意义讲谎话一样)。亲属之间因为争利益而出现矛盾,关系不和谐了,才会有要求孝慈的各类规定。国家处于混乱的时候,才会显现功臣的力量。在平时的安定环境里,功臣的功效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有没有功臣,国家一样可顺利发展。
《老子》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不要推广圣人的事迹,因为圣人的行为是特例,平常人难以做到;不要宣扬各种弄乖使巧的事例。这样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推广圣迹和巧智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令社会操作成本加大、效益降低,因此民众的获利就相对减少。(典型的就是部分人先富起来让社会趋利,不公平,道德沦丧,结果大众的利益相对减少,大大跟不上GDP的增长速度)不要提倡仁义,因为提倡仁义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人际和群体的关系要和谐融洽必须恢复至“道”的原理上,那就是初始的原始社会阶段的公平状态。这样人际关系自然就会有慈孝了。取缔奢侈品生产,让民众没有获得利益的途径,则社会将没有盗贼。(毛泽东时代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三段言论还是不能说明“道”的社会学原理。因此还要附加在说明一下。要弘扬朴素的精神,保持人类社会刚进入文明时的公平状态;要倡导大公无私减少私心,要减少欲望知足常乐;不要学习那些投机取巧的事例,以公平厚道的心态对待事物,则不会有什么令人担忧的事情发生。
本章的要点是讲述在社会学上怎么运用“道”的原理来达致公平和提高社会效率。
《老子》第二十章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恍兮,其若海;恍兮,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阿:大的山陵 。唯:急速回音
对之高山呼喊,听到的回音与呼喊的声音究竟有什么分别?赞美事物与贬低事物对事物发展的影响又有什么差别?对于公认的影响和威胁,我们不能意气用事不管不顾。(慢、恶、死等等都是人所畏惧的)大地看起来荒芜,是因为还没有插秧耕作。(事物的发展有本原和现象两种不同的因素,这两种因素有时会相互转换的因此要仔细分辨)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
众人兴高采烈,拥挤着去享用祭祀后的牛肉大餐,这状况好像春节争着登上高台欣赏景致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跟随大流,独自静止没行动,就象没有经过火灸的龟壳,没有征兆。
“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恍兮,其若海;恍兮,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我静止的状态犹如刚生下的婴儿还没有叫喊;又好像长长的丝线不知道那线头要归落何处。众人的思想和主意都很多,而我对世界却有很多不知道和存在很多的疑问。我实际就是愚蠢的人啊。大家都明白事理,我却昏昏然不知事物的始末;众人都能仔细观察分辨事物,而我却不能对事物发表什么意见。我经常走神,有时思绪象江湖河海般汹涌,有时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总是难以让思绪停顿。众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和达到什么目的,而我却与别人不同,我所重视的是我的身体,我在想着怎么让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
注释:食母者乃人的身体,于内为胃。调养身体让身体健康,辟谷食气是高层次的“贵食母”
《道德经》注解(7)
《老子》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孔:(象形。金文字形,象小儿食乳之形。婴儿吃奶容易过量,因以表示过甚之意。本义:甚,很)恍:有。惚: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甚大,教孔丘为知。後世不信道文,但上孔书,以为无上,道故明之,告後贤。(《老子想尔注》张道陵)这是一种说法,但有点牵强,因为崇善儒学是董仲舒以后才开始的,为此埋伏笔或者作说明的可能性不大。
很高的德行,很好的品质的实质(或内容),都是遵循道的原则而得到的,只有遵循道的原理,才能有好的德行好的品质。道表现为具体的事物形态是有和无,有时是有,有时是无。在有无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时可看见现象,有时可看见实物。道处于深远昏暗的地方,难以观察。但是道有它自己的精华,这样的精华是实际存在的。道表现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从古到今。道的作用和功能在实际的社会实践中为人们所感受,水都不能否认道的存在。它贯穿于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之中。我怎么知道事物发展的初始状态呢?那是因为我掌握了道的原理,用道的原理和规则来观察分析事物。
本章要义是讲明道贯穿于事物的发展过程,是世界的本质。以道为准则就可以轻松的解决问题。本章难点在对“孔德”的理解上。
《老子》第二十二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弯曲的树木因为不成才而不遭受砍伐而得到保全;木材弯曲就会遭受刀削斧凿,甚至还会遭受火烤,因为人们需要直的木料;地势低的地方在下雨时就会积水;老旧的事物会得到翻新或重建;缺少的东西在自然环境里就会自然补足(如干燥的东西放于自然环境就会很快吸收空气中的湿气);多得,或者某方面具有很多的就会迷惑(如老婆多的人会有很多烦恼,钱多的人会担心损失或遭受绑架)。因此,圣人会坚守“道”的原理,并将道的原理用于治理天下。不自认为自己的见解正确的人就可以多听别人的意见,因此就可以全面的了解事物;不自己肯定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是有德行的人,只要成绩出来,别人自然就会肯定和表彰这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不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进行征伐,那么人们就比较容易认同他的功劳,而如果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进行征伐则很难获得认同和立功;不自夸显露自己,就会有机会获得提拔或者有机会增长自己的力量。这一切全都是道的原理,道就是顺其自然,与世无争。就是因为与世无争,天下的事物和同类都难以跟无争的人相争。古代人所说的“曲则全”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原理,那并不是虚言,而是按照道的原理行事的结果。总结的结果是事物要周全,必须以原有的真实显露,顺其自然,不要太彰显自己的长处才能获得保全。
本章要义在于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例子说明强出头或者强行表现会招致祸害,顺其自然按天理行事,不盈满则能安全。这符合“福莫大于无祸”这样的传统观念,只有保全自己才有其他的各类附带要求可讲。人没了,或者病了则有再高的官或者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处。
《老子》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就简单的来说一说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吧,旋风或者暴风没有整天刮的;暴雨也没有整天整天下的。狂风暴雨的发生都要有间歇。引发狂风暴雨的是什么原因,那是天地的运作。天地的作用尚且不能够让狂风暴雨持续一天这样的短暂的时间,那么人的能力比诸天地又有所欠缺,又如何能够让事物长久呢?因此,遵照道的原理做事的人,与道相近;按照道德原则来做人的人就与德性相符;施舍施行慈善者的行为就等同于慈善。遵照道的原则做事,可以从“尊道”的做事规则中获得乐趣,也能够较容易得道;按照道德修养做人的人可以在帮助别人与改进自己的品行中获得乐趣,因此德性会逐渐增加;从事慈善的人会在做善事和施舍中获得快感,自然的也能够在社会中获得慈善家的名声。道、德、慈善要身体力行,如果不实践你怎么能够说它们无效呢?
本章要义在于提出道、德、慈善三种高尚行为,并从自然界中的现象说明什么都没有长久的效用,连天地都无法保持长久的效用。虽然没有长效的行为,但讲道德和行善有乐趣,只有自己进行实践才能知道其中的乐趣。理解本章的关键是关于“失”的定义。这要结合整个章节的意思来理解。
《道德经》注解(8)
《老子》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踮起脚的肯定不如站立的人坚持长久;打不行走的人肯定不如正常走路的人持续时间长。坚持己见不听别人意见的人,就难以有正确的判断;经常肯定自我功劳的人难以获得认可;因自己的理由而与人争斗,别人是不会同情和认可的,只有见义勇为才能获得社会表彰;自己老是夸奖自己的人是难以获得社会认同和改善自己的处境的。这些事实的道理在于有没有遵守“道”的规则。有这样的结论:“浪费粮食;身体有多余的赘肉;迷恋物质,都是不符合天理的,也是不符合‘道’的原理的”因此,有道德的人,是不会浪费粮食,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多长赘肉的,也不会迷恋物质。这些不符合自然的事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做的。
本章要义:再次强调要顺其自然,不要做违反常规的事。要珍惜粮食和身体,不迷恋物质,因为这么做才符合“道”理。
《老子》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一个东西混然而成,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寂静而空虚。它独立而没有变化,周而复始的起作用。它可以是天地的母亲,我不知道怎么命名它的名字,因此就勉强把它叫做“道”;勉强称呼它为大。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消亡,消亡就是逝去;逝去的事物就会随时间流逝而被人们不理解;以前发生的事物再出现就是事物的发展周期。因此具体到某些事物里面的道也有显露被人观察得到,再到难以被观察这样的发展周期;天、地和君王都一样,也有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发展周期。世界中有四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周期,人就是其中的一种。人类社会可观察依据的是地球;地球发展所依据的宇宙的发展规律;宇宙的发展要按照“道”的原理来进行;道的基本原理贯穿于自然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从自然演化中发现道的规律,按规律办事。
本章要义是讲明道贯穿于事物的发展过程,道是世界的本原。人们要了解道的原理必须从自然界的演化规律中来总结。
《老子》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辎(zī)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轻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但两者是有联系的,重是轻的根源。(看水与水汽,再想象一下不倒翁就容易明白)静与躁也是对立的概念,这两者也是有联系的,静是和谐是色彩分布均匀,躁是病态是躁动。在养生学的理论来讲,人体的基本健康状态是均衡是静,而躁动就要生病,因此静为躁君。由于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君子会利用相联系的事物来为自己服务。因此,君子每日的行动都要借助工具。如出行借助车辆、行李。君子处世,虽然有繁华的景物可观看,但会象燕子筑巢在屋子上一样,根本不会在乎屋子是否华丽,而只在意于巢穴是否安全和避雨。为什么有万乘军车的国君要蔑视民众的生命发动战争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行为就是将自己这样的轻来与天下百姓这样的重来相互作用,这样的结果明显,胜负立判,只能自取其咎。轻易发动战争则会失去根本,因为不重视民众的生命;躁动发动战争就很容易失去统治地位。
本章要义是讲明道怎么使用在治国方面。要分辨轻重,这在《管子》中就有很多章节专门说明轻重。分辨轻重就是要辨明什么是主要矛盾进行处理,不要本末倒置。
《道德经》注解(9)
《老子》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恒善救人,故无弃人;恒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袭:衣一套为一袭。“是谓袭明。”袭,常明也,能知此意明明也。(《老子想尔注》张道陵)因袭,照旧搬用。“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韩非子?孤愤》
善于行动者别人是难以看到他完整的车的轨迹,因为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改变交通工具和采用不同的运动方式;善于言辩者,他们的言论没有什么语句的毛病和举例的毛病;善于计算的人是不需借助筹码和典籍的:善于设置锁类机关者,不告诉别人开机关的关键别人是开不了的;善于结绳者如果不告诉别人怎么解开绳子,别人是无法解开他结的绳子。这些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并抓住关键问题来处理矛盾的实际事例。同理,圣人的方法也是抓住关键。他们平常救人、助人,对什么人都一视同仁,因此在圣人面前是没有什么人是不可救助的;他们善于利用道的特性来帮助事物的顺利发展和解决,因此在圣人面前并没有什么是可以遗弃的。这样全部透彻的了解事物的特性和发展原理就叫做“袭明”,因此善于帮助别人的人是教会别人谋生的机巧;不善帮助人的人是资助别人以钱财。不将自己知道的某些技巧看得很珍贵不肯教人;做慈善时不要老是资助别人的钱财,要教会别人的谋生手段。这样的方法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是不明白的。这就是做慈善的要点。
本章要义是讲明做慈善的方法,要“善人之师”,不要“善人之资”。道的方法是抓住关键。
《老子》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雌雄,黑白等是道家养生的重要概念,都是由阴阳概念演化而来的。古代贵族生活稳定,因此追求长寿,故而对于养生的道理很容易接受,老子为了说明道常用养生道理来阐明道的原理。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了解雄性的特点,就知道对雄性来讲什么是损益,要趋利避害;了解阴阳互补、阴阳相吸的原理就知道守阴养阳的道理。照这样的道理做是世人养生主要方式。以这种方式行事,可以长期保存获得精气的来源,也可以不让元气损减。长期坚持就可以回归到象婴儿刚初生时的状态。”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精白与元炁同色,黑太阴中也。於人在肾,精藏之,安如不用为守黑,天下常法式也。”(《老子想尔注》张道陵)
知道元气和精气的重要,就要保持好肾脏的健康,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不放纵。自然的,人通过节制增加修养就可以健康长寿。这样方法可以成为养生的定式。遵照这样的养生方法生活,则可以增加道德让身心愉快,不会有什么差错发生。这样人就可以达致那种虚无的状态。(长期的守静、虚无,人就接近道的状态,就会自然的出现各种超异的功能,如预感、返老还童、躯体变化、腾空等等。)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
看到荣华富贵,就知道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得失并不在于荣华富贵,而在于心情是否愉快。如果因为追求荣华富贵而遭受惊吓,那是很不合算的。守住自己的欲望,不要有太多的奢求,就不会有什么耻辱发生。也不可能因社会纷争而遭受惊吓。“人若无求品自高”。宽容大度是天下人行道基本要求,照这样的要求行事就可以积养成充足的道德,道德淳厚了,就复归到接近于道 “朴”的状态。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道德积累多了就像成材的木料,木料去皮加工就成为有用的器物。有道德的人是人才,圣人肯定会使用,而且会根据需要和实际的情况任命为官长。因此成熟的制度是不会舍弃那些有道德的人的,肯定会重用有道德的人。
本章要点是讲述个人怎么运用“道”来健康生存和适应社会。坚持不争、积德的行事方式,社会自然会寻找启用有道德的人。
《老子》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随;或噤或吹;或强或羸(léi);或培或隳(huī);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隳:毁坏;崩毁:“隳人之城郭。”羸:瘦弱:羸瘦。羸困(瘦弱困顿)。
道没有具体形态也难以定义,很难以具体描述。想将用道来治理天下并广为推广,我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天下是自然演化的神奇系统,它不是什么人可以强行干预和改造的(这里面暗含现代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概念,生产力不发展光设想高层级的“共产主义”也没用,只能遭受失败,要按实际的生产力来设定生产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执意要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改造社会,那么必将失败!如果强行抓获或惩治那些不按自己意愿办事的人,那么统治者就必然会失去统治地位。一切事物的特性是两方面的,有些人领头,有些人跟随;有些人不开口,有些人讲话吹奏;有些人强壮,有些人羸弱;有些事物得到关心和培养,有些事物就要遭受砍伐和毁坏,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因此圣人的办法是不做过分的事;不追求奢侈;不追求想得到泰卦,因为泰卦上地下天有悖常理。虽然从解卦的卦辞爻辞来看需要从下往上解释,但总卦象与上天下地的自然景象是相违背的,即使不错也希望得到这样的卦。(泰:天地交。但顺序逆反)
本章要义:道不可强行推广。事物发展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想完全没有负面的是不现实的。而且好坏是会互相转化的。
《老子》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得已,果而不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以道的原则来辅助君主的人,不会以战争来称霸。利用战争称霸没有什么好处,必定有坏的回应。例如出兵外国,军队索道指出会遭受民众的阻击,就像人走进荆棘丛中;而且在大规模用兵之后,国内会有粮食歉收、造反、骚乱等不良现象。因此善于运用军事优势的人,只是利用军事优势达到目的,不会真的用战争的手段来达致目标。达到目的后不会骄横;达到目的后不会自夸;达成目的不须用杀伐的手段获得;胜利的成果不是一次性而是有持续长久效用的。达到目的而不必使用粗暴的战争手段。事物发展到顶峰就会衰落,这就叫不符合“道”,不符合“道”就不能长久,会很快的衰亡。
本章要义强调不要用武力来强取豪夺,因为使用武力会有不良的后果。最好获得利益的手段是通过公正和平的手段来获得。
马王堆帛书: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得已,居是谓,果而不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就是说多了一个“处于这样的状态可以说,不用用强而达到目的”
《道德经》注解(10)
《老子》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弗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铦(xiān)庞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
|
|
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铦:形声。从金,舌声。本义:田器,臿属。一种农具。庞:形声。从广,龙声。广(yǎn),象高屋形。本义:高屋)
④銛:利器,即兵器。 龐:《馬王》甲本辨爲“襲”,《道藏》甲本辨爲“龐”,?原件“龍”上一點一橫?明顯,左側亦似有撇,其下無“衣”旁,故“龐”者?確。《說文》:“龐,高屋也”。銛龐,有刀槍入庫之義。乙本作“銛龍”。通行本作“恬淡”。
武器装备是不详的器物,有这样的物品就有坏事出现。因此有道德的人不会使用这样的器物。君子正常生活中喜欢使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古代中国有左阳,右阴的概念),使用武力则属于阴性不良的手段。因此使用武器装备不是君子的办事方法,因为兵器是不详的东西啊。武器装备最好是象农闲时的农具一样收藏在仓库里,不能老是惦记着改进武器装备。若是整天的惦记改进自己的装备,则是喜欢杀人的人。喜欢杀人的人不可能获得天下人的认可,也难以获得成功。因此,我们在办激情事的时候喜欢用光明正大的方法;办丧事时则用操办阴事的办法。因此,在军队中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偏将军不专煞生之机,像左;上将军专煞,像右。)这就是说在军队中的任职机制是照丧礼的习俗来办的,因为军队是杀人的阴性行业。战争胜利了就要杀很多人,杀的人多就只能以悲哀哭泣的态度来对待。战争胜利后就应该象办丧礼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本章要点:“夫兵者,不详之器也。”是中国古代先人根据宇宙系统论总结出来的军事结论,这个理论与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军事观点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观点,才没有穷兵黩武,才能成为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国家。
《老子》第三十二章
道恒无名朴,虽小,天下弗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也。
朴:本义:树皮。《说文》:“木皮也。”
道通常是没有名称、也没有形状。道即使再卑小,天下也没有什么可以能让“道”臣服。侯或者王如果可以坚持用道的原则做事,那么很多的人和事物都会自己来归附。天地相交,产生了甘露(喻指自然界中各种可以维持生存的物品),人民在没有什么制度和号令的时候就自己可以公平分配了。当最初的制度被创制出来,创制出来后又被推广使用,这样人们就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知道分寸和规则,不混乱做事,社会就有了秩序,有了秩序的系统就可以周而复始的运转,因此就没那么容易消亡。这好比“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也好像河道川谷规定了水必须流入江海的道理一样。
本章要义讲明了社会制度与秩序的重要性,有规章制度才能有公平的社会秩序,有好的秩序,社会就可以和谐发展,社会能和谐发展就可以持续。
《老子》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了解人性特点和欲望的就叫做智慧,但连自己的特性和缺点都了解的人才可以称为完美的智慧。能够战胜别人的我们称为是有力量者,但那些能够克制和改造自己弱点人才是真正的强有力者。知道欲望无限,人生短暂会克制自己的人是精神富足者;有确定目标并坚持不懈的人是有志气的人;不失去其生存发展根本的人就可以长久发展和生存;死亡了还有人积德和怀念的人就是不朽。
本章要义:用全面的系统论观点阐明人际社会是完整的系统,个人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凡事不要盈满。
《老子》第三十四章
大道汜(sì)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衣被万物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知主,则恒无名也,可名为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其大。
大道充满事物发展变化之间,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左右。万物依赖道的原理而存在,事物顺利发展之后看不到道的存在;(“万物恃以生而不辞。”不辞谢恩,道不责也。)道象人类的衣服一样,包含于所有事物发展中,但道并没有显露。因此,道是没有欲望的,可以将之称为小。所有的事物发展都要依赖“道”,但却没有显露出主宰的特点。因此道在事物发展中没有名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大。这样,圣人之所以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成为领袖这样的想法,因此他们可以自然的成为领袖。(为民众利益而不为己)
本章要义:道的精神是养生而不居功,助人而无己欲。阳光和空气的功能就是道的精神。
《道德经》注解(11)
《老子》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大:大指“道”(前文)
按照道的原理治理国家,则天下的百姓都会归附向往。大家到来后都不会有受到
|
|
什么损害,因为道的精神就是“生生”。不遭受损害就可以平安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和美好的食物会让所有的过客都有停下居留的意愿。道的功效的显示是淡而无味,难以觉察的;我们要观察但难以发现;我们要想仔细听则难以听到道的声音;我们用道的原理则发现不了道成功后离开的迹象。
本章要义:宣扬“道”的精神,并说明道的治理作用。“执大象”因此为历代中国人所效仿,因此而推广道了很多日常生活中。历代陶瓷的象耳瓶就是为了显示“执大象”精神而创造的。
《老子》第三十六章
将欲歙(xī)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之胜刚;弱之胜强。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歙:这个词字典都难以查找到原意。潮汕词语中就有“歙”这个词。意思为“塞进”。 “将欲歙(xī)之,必固张之”是木匠的榫卯工艺名称。潮汕人很容易理解这个字。
想塞东西进物体里面,必须先将物体撑开;想削弱某一事物,必先固定它(车床工艺);想去掉某些事物,必须先让它兴盛;想夺取别人东西,必须先给别人小的好处。这些就是细微之处的明察。柔可以克刚(水滴石穿);弱可以胜强(绳锯玉)。鱼是不能脱离水而生存的,国家的有利武器是不能够轻易显示出来的,因为它的功效显露之后人们就知道怎么防备。
本章要义:用事物发展常理来说明怎么将“道”理运用于实际生活之中。
《老子》第三十七章
道恒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我们通常看不到“道”的作为,但“道”的作用又无处不在。君王如果可以坚守运用道原则来治理国家,则万事万物将和谐相处自然发展。和谐相处自然发展就可以引导民众恢复到原始的淳朴上,只要恢复到原始淳朴状态,则民众就没有欲望,没有欲望的民众组成的社会是安静稳定的社会,这样的秩序下的天下那是理想的社会。
本章要点:可以说《管子》和《老子》是中国和谐思想的来源。顺其自然达致和谐安定是道家的追求。
《老子》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rǎng)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注释:失道而后德说明德是随道而生。“德莫大于生生”,德之要义在于生养。古代德与得是通假字,因此德也有“得到”的含义。
最好的德性,大家看不到它们的作用,但是却实际是万物生存所必须的。(如水、空气、阳光等)有最好德性的事物是难以觉察到的。次一级的德性是不失去德的本质,也就是“生养蓄”功能,在这样的德性哺育下我们没有感觉到有德。(如母亲的生育)最好的德性是什么都不做的,因此它们不是为什么目的而存在,但事物都要依赖它。次一级的德性,也不可以去做什么事,但人们却可以观察到过程和目的。(如生育)最高级的仁慈义举是人们感觉不到有什么特别行为,但生活却因此而改善。(如西藏的农奴解放,西藏民众觉得自然。但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功劳)最好的义举(失仁而后义,因此次一级的仁就是最好的义),大家可以认识和感觉到。如均贫富,建立公平分配制度。(新中国建立)最好的礼节做出来,大家都没有回应(不必回应)。因此说“双手揖礼,而人们不觉照常行动。(宾馆服务员有礼貌大家不觉得,但是没有了这样的礼貌人们就会觉得宾馆的星级不够)因此,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讲,失去自然的道德规范后人们就会要求讲道德;失去道德规范的功效后人们就会讲究仁慈来规范行为;没有了恻隐之心的仁慈心态后,人们就要讲究什么是应该做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如果社会连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标准也失去后,人们就应该讲究礼节。礼是相互尊重的一种方式,忠和信已经几乎没有了才需要礼。因此有了礼就说明社会要乱了,因为原来维系和谐社会的各种基本原则道、德、仁、义的作用都很薄弱,只靠相互表面的尊重来维系是不行的,人际间的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
提前知道和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是“道“的精华,但也是愚蠢的开始。因为什么都预知或已有防备措施,人的反应就会减慢,也会丧失一些原有的能力。(如美国人从小学起就使用计算器,现在的数学水平就极为低下)因此大丈夫为人处世要遵从道德仁义,不要表面上讲究虚伪的礼貌;遇到什么事要以坦然的心态去面对,不要老是打探事情,因为那是对自己不利的。(如在单位里老是打探别人或老板信息的人就很难获得提升)因此我们生活中要坚持本性,不要去学习那些看起来以为可以有助自己的机巧。生性淳朴的人自然的就可以有好的前途。
本章要义:讲明社会维系的秩序按照道的原则来进行,而道之后的德、仁、义、礼等演化都要依照道原理来进行,不要舍本逐末。顺其自然是乐观人生态度,如果能够坚持则身心愉悦、事业顺利。
《道德经》注解(12)
《老子》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得一以为天下正;万物得一以生;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谓地无以宁将恐发;谓神无以灵将恐歇;谓谷无以盈将恐竭;谓万物无以生将恐灭;谓侯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必以贱为本;高以下
|
|
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是其以贱为本也。非欤?故致数舆无舆。是故不欲琭琭若玉,珞珞若石。
那些得道者会有什么表现:天得道可以清澈;地得道可以宁静;神得道有灵验;谷得道可以充盈;侯王得道可以成为天下的正统;万物得道就可以很好生长;这些都是因为得道而带来的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天如果不清澈恐将发生裂变;地如果不安宁就要发生地震;神如果不灵验,那么人们祭祀神仙的香火就将停息;山谷如果没有流水充盈,就会显现枯竭的状态;万物没有生机,世界就将毁灭;侯王如果名不正,则将遭受挫折。因此德的基本原理是富贵的要以贱为本;高的要以下为基础。因此侯王自称为“孤“、“寡”、“不谷”。这是以贱为本,难道不是吗?因此,低贱的奴隶阶层往下就无法再区分层级了,但是他们却是生产的根本。因此说宁肯象泥土,也不要象闪光的玉或象坚硬的石头,因为泥土可以种植,具备有生的德性。
注释: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玄通真经》
本章要义:要理解德的含义才能理解本章。从德的本意出发就可理解为什么说不要象玉石。
《老子》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注释:“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是道在起作用;道的作用是微弱难发现的。”这是常用的白话注释。但含义与上面的有些章节重复,惜墨如金的老子应该不会这么写文章。
反对者出现是道在起作用的表现(不符合自然,过分了就有反对者。这是用道的重要准则),弱小者是用道的基础(历代王朝替换都是发动农民起义,或者利用反对者力量来达成)。天下万物都生于有(有了名称才可分辨事物,事物因为有了才能够呈现演化发展的过程)有生于无(这很难理解,现举例说明一下。例如一个人与一个人合作表面是一加一,应该等于二。但是一个人与一个人的合作应该大于二,为什么?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争斗成本减少了,这就是多出来的合作利益。这就是“有”从“无”中出现的一种例子,多出来的“意外”利益是从合作机制中得到的。)
本章是道德经的重要章节,虽然字数少,但原理很重要。事物出现反对者就说明有不合理的因素,这就是道在起作用。最弱小的是社会的决定力量,不能忽视,照顾到社会弱小的利益,社会才可正常的发展。“有”、“无”、“弱小”“反对”这些因素是遵从“道”的人要注意的。毛主席就是悟道的高手。
《老子》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lèi)。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婨(lún)。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yú);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注释:自马王堆帛书出土以后很多的人都认为是“建德若偷”。但是整体的含义还是不符合本章节的含义,故而还是采用“建德若婨”版本。纇:丝上的疙瘩
聪明的人听闻道后会认真的按照道的原理来行事;中等聪明的人听到道之后,会将信将疑;不聪明的人听到道的“无为”原则以后会大笑,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无为”可以取得成果。因此有著书立言者说:“明白道的原理者行事象糊涂人(因为不大计较得失);明白进取原理的人行事象是在做退让的事(做官谦让);平坦的道路在远处看来是有起伏的。最好的道德建立起来后看起来象是山谷,有很多需要补充的(毛泽东建立的国家);广泛普及的道德又好像很不足(也是毛泽东时代的生活,人们生活好像很缺乏物资,但大家都不担心自己的生活);建立好的社会道德就好像是培养一个大家闺秀(琴棋书画、女红、德性教育等是需要逐渐教育积累起来,不能一蹴而就)。本质纯净优美的好像发生改变(纯净水变蓝、猫眼石变色);很白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有不纯净(如光线很白,但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物体上就有不同的色谱。大白若辱是古代人认识光现象的一个文字记录)大的方形建筑物看不出来有角落(天安门、故宫);大器物必须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做成;大的声音好像听不到(如地震的声音);大的形象就难以描述具体形状(如大地。也可以理解为:大道的形象是看不到的);“道”是隐蔽的难以有具体的形态。就是这个道,它非常善于开始,也善于结束。
本章要义:讲述道在人际社会中的运用,讲明道是隐晦的,有时与实际的发展态势不符,但只要遵循自然发展的道理就是按“道”行事,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称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亦议而教人。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学父。
道是世界的本原,也就是一。道演化出阴阳二性;阴阳结合演化出世界万物。万物都是阴阳的结合体;阴阳结合好像两股气流结合互换,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展现出来的就是事物的本性。人们最为厌恶的就是孤、寡、不谷,但君王们都喜欢用这样的词语来自称。这是因为事物的发展道理是“损之而益”(古代中国人都认识这道理,很多人生小孩起不好的名字是为了好养育就是这道理)。因此,事物是你贬低损害它,它越是生长旺盛;你褒益某一事物时就会损伤它。前人的教育我们也可以分析讨论后拿来教育别人。强横突出者不能够有自然的寿命,必遭挫折横祸,这是我们应该谨记的教训。为人莫要强出头。
本章要义从道的原理说明事物是由阴阳两个方面组成的,枪打出头鸟,强出头就要遭殃。因为天理是损盈补亏。故柔弱可得天助。
《道德经》注解(13)
《老子》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
天下最柔软的东西就是水,水可以驰骋于坚硬的岩石之间。没有实在形体的东西可以进入看不出有间隙的地方(空气)。我之所以
|
|
知道“无为”是有益的,就是从水和空气的作用中感悟到的。不用言语教育而以身作则,就是“无为”教育的典范,是很有益处的,天下没有什么事物可以超过“无为”这样的做事原则。
本章要义: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其自然,从最初的形态起切入施加影响。这好像我们教育别人不要用言语而以身作则一样。
《老子》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名誉和生命哪个最可爱?生命与财产哪个最重要?得与失哪个害处最大?因此什么事过分热衷爱恋就会浪费精力物力;有过多的财富和珍藏就必然要出现大量的陪葬,而陪葬品多又会出现后世掘坟等扰乱死人的事发生。因此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受耻辱;知道做事适可而止就不会那么容易失败,就可以长久的发展。
本章要义:就道的原理推导德性,说明德性的建立摆脱物欲和名利,知足者常乐,知止者不殆。
《老子》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诎(qū);大辩若讷(nè);大巧若拙;其用不屈。躁胜寒,静胜热,清静可以为天下正。
大的成就好像总有缺陷存在(如新中国建立),但这成就的功效可持久延续;大盈满好像整天流失(黄河长江),但我们不管怎么使用都不会穷尽。很直很长的线或物看起来象弯曲的(铁轨、地平线);很会与人辩论的人看起来好像不会说话,但他们说话时别人辩不过他们。很有智慧的看起来有点笨拙(爱因斯坦);但这些表面看不到的优点,却又有很好的用处。人抵抗寒冷时运动;抵抗热的环境则需要安静。清可以保持纯真品行,静可以让身体机能协调,保持清静可修生养性,修身养性可以积德,持续保持自然可成为天下的榜样。
本章要义:用常理来说明德性的修养需要清静,不能追求名利。先正己而正人。
《老子》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懵(měng)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如果天下都能按照道的原理来做事,那么军队使用的马匹就会作为农耕之用。如果天下的人不按照道的原则办事,则民众会相争斗,为了争斗必须准备战马,因此在城市的郊区就会饲养军马。最大的过失就是纵欲;最大的祸害就是不知足;最容易惹祸的就是不明智的追求过分的目标。因此有节制的满足就是长久满足。
本章要义:从不尊崇道的原理办事,到出现军队相争,把可以用于生产的人力物力用于相争斗。来说明道德要求人要节制,要为别人留存生存空间和条件,要公平。无论事国家和个人都要为别的个体考虑,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具备高的德性。
《道德经》注解(14)
《老子》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yǒu)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明;弗为而成。
不出门户,就能够推知天下的事理;不望窗外,就可以认识日月星辰运行的自然规律。这是通晓道的原理的人可以达到的境界。那
|
|
些离开道越远的人则知道或了解事物的规则就越少,道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因此圣人不用出行就可以知道天下事;不用见到事物就可以知道事物的发展动态;不用自己行动就可以指导成功的实施计划。
本章要义:“道”理是认识事物的方法论,离开了“道”的原理就很难认识事物的本质,离得越远则知道的越少。有了“道”的方法论则不须远行而知天下事。
《老子》第四十八章
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则无不为。将欲取天下者,恒以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注释:这章节经常断句为“以致于无为,无为则无不为”因此会出现理解上的错误。
搞学术研究采用的方法事逐渐的增加知识,因为对问题认识和见解是不断积累的。但是,如果作为方法论来讲,则需要采用“损之又损”一层层剥离到达事物初始状态的方法,来追求事物的本质。采用这样追逐初始状态,寻找解决事物问题和矛盾的做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事物。如果要获取天下,则要坚持从“无”这样的初始状态出发来解决问题。 如果不追求民众根本的目标来解决问题,则很难获取天下民众的信任,因此也难以领导天下。
本章要义:这是道德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就是层层剥离找出影响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就可以顺利的处理一切问题。
《老子》第四十九章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矣。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矣。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浑焉,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圣人通常没有个人的意志和欲求,他们总是讲百姓的意愿堪称事自己的意愿。对善良者,以善良对待;对不善良者也是以善良的措施对待。这样就得到为善的结果,也可带动社会乐于慈善的风气。对于守信用的人,圣人信任他;对于不守信用的人,圣人也信任他,这样就可以再社会上树立起相互信任的好风气。圣人的行为在于为民众做辅助工作,这好像事木匠工作中最基础的“歙歙”;圣人的任务像是为了保证河水的流量正常。圣人的行为百姓都看再眼里,这起到以身作则的教育作用。而圣人眼里百姓则象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本章要义:“与民同心”是治理的关键。为人民服务是根本。毛泽东就是圣人!
《老子》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之厚也。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sì)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惜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注释:这是道德经难以理解的章节,有很多的注解书都错解了“十有三”的含义。而要精确的了解十有三,必须了解道家的养生观念。四肢九窍是道家养生很注意维护的部件,而十有三是一种加法描述,古汉语的十有三就是13的意思。道家认为九窍四肢的维护和保养是养生重要手段。“凡之生生,而生者固动,动尽则损也;而动不止,是损而不止也。损而不止则生尽,生尽之谓死”,不节制多动不行,不动也不行。
人生从生到死,长寿的因为会保养四肢九窍因此而长寿;早夭的人也因为不注意保养四肢九窍而短命。而且民众为了养护自己的身体必须行动以获取食物,人类行动从总体上来看是: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但总体是朝着死亡迈进的。归结起来也是因为四肢九窍这十三个器官的原因。为什么?那是因为很多人的生存是为了四肢九窍的满足,也就是欲望的过度满足,一纵欲就容易过分,过分就要衰变。据说,很善于养生的人,在陆地行走不会遇见犀牛和老虎这样凶猛的野兽;处于战争中也不会遭受兵器和士兵的伤害。犀牛没有机会用角老冲撞;老虎的爪牙也不能对人使用;士兵的兵器也没有可砍伐的对象。为什么啊?这是因为善于养生的人会避开猛兽出没的地方,即使需要到猛兽出没的地方也会找猛兽不出来的时间去,同样的道理会养生的人再战争中也不会遭受伤害,因为他们会避开那些导致人死亡的事和地方。
本章要义:从众人容易理解的养生道理说明道德与养生一样,要因地制宜,要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不能教条僵化,要活学活用“道”的原理。
《道德经》注解(15)
《老子》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度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
道生成万事万物,德养育
|
|
万事万物。事物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事物发展都有一定的框架和规矩来限制事物的发展。因此万物尊崇道的规则而提倡德性。道的尊崇,德的珍贵,是难以衡量的。(道德似水,故用“莫之爵”来说明八百一衡量)只要顺其自然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有道德。所以说道衍生出万事万物,德要积累;德是生长;德是养育;德在于公用;德是宽容;德是覆盖庇护。德生长事物而不不显露;德帮助事物发展而不居功;德帮助养育而不进行宰割。这就是最高深的德性。
本章要义:道和德要顺其自然才可得。道与德并不是象酒水一样可以用爵器来装。也就是说道与德不能够从别处移来,只能自得。要得道德必须靠自己,即使是自己的父辈也不能够传授道德。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可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
天下有始,可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天下初始,万物开始有了名称,这可以说就是万事万物的母亲(根源)。既然知道的事物的根源就可以据此来推断它们的儿子(从属)。从事物表象回头追寻根源,我们就可知道事物的发展规律,这样即使到死的时候也不会有危险。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塞:(会意兼形声。从土,塞(xià)声。塞同罅,空隙之义。本义:阻隔;堵住)。兑:交换:兑换(用一种货币换另一种货币)。兑现。汇兑(两地通过信件或电报交换款项)。 液体从一个容器注入另一个容器,一种东西搀到另一种东西里去:兑点热水。门:天门百会,房子的进出路径。
阻隔事物相互混淆的路径,区分事物的界限,再分析事物的初始状态己发展路径,找出解决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方法。只要这样为人初始就终身都不会很劳累。找出主要矛盾后,要考虑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利用事物间的相互影响来解决主要矛盾,则终身都不会遭受什么难题的阻碍。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
能够见到微小物体的我们称之为“明”;可以守住柔弱地方的就可称为强。解决矛盾的办法就像我们平常使用照明,反过来再追溯光源。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就不会留下什么祸害自己或身体毛病。这就是沿袭常理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章要义:“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就象“损之又损”是重要的方法论。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不要混淆;考虑事物相互影响的相关因素再加以利用。
《老子》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竽(yú),盗竽非道也哉!
介:象形。甲骨文字形,象人身上穿着铠甲形。中间是人,两边的四点象联在一起的铠甲片。本义:铠甲。一种用来防身的武器)
假如我们拥有大“道”这样的知识,并且理智行事,一切都按照“道”的原理来做(治理天下)。但还是有问题:“道”的原理是难以认识的,而且普通人则大都喜欢走捷径(好逸恶劳)。朝廷宫殿规模巨大,梯阶很多;而田地则因建筑宫殿用过多人力而没有人力耕种,造成荒芜。因此仓库空虚。而统治者仍穿着锦绣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饱餐精美的饮食,搜刮占有富余的财货。这就是在倡导强盗的抢夺原则。这样由统治者带头的倡导好逸恶劳的作法,并不是道。
本章要义:即使“道”的原理统治者明白也难以按照道的原理做事,因为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难以更改。什么统治者都不会放弃放弃鱼肉人民的。
《老子》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馀;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善于建树的不可能拔除,善于抱持的不会脱掉。(善能以道建国立本者,不可倾拔也。善能以道怀抱百姓者,不可脱离。《唐玄宗注解》)子孙要坚持祭祀,保留感恩的心,这样就能有好的传承。(子孙的祭祀功能犹如善建和善抱者。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爱其甘棠,况其子孙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兴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虽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毁庙之主,流溢於外,而後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辍,止也。《唐玄宗注解》)德的修养从自身开始,就可以得到纯真的道德;讲德的修养扩大到家庭里面,那么德就会有余;再将德的修养扩展到乡里面,那么德的功效就会扩大;而将德的修养扩充到邦,则邦的得能够会丰盛,溢出影响四周;德性修养推及道普天下,那么德就能广泛的发挥作用了。因此,以个人观察个人;以家庭来比较家庭;以乡村来比较乡村;以城邦来比较比较城邦;用整体观念来看天下,就可以知道德性修养要怎么进行。我为什么知道天下的发展规律和运行道理,就是照着道的原理来进行考察的。
本章要义:德性是生养,大家都知道修养德性,就可以共同努力的生产,也可减少纠纷。德是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只有生产力发展才是解决旧社会问题的根本,而生产理的发展又有赖于人们对于生产进步(德性)认识。
《道德经》注解(16)
《老子》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蜂虿(chài)虺(huǐ)蛇弗螫(shì);攫鸟猛兽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而朘(juān)怒,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精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很有道德的人就好像知刚生下的婴儿一样。刚生下的婴儿毒蜂和毒蛇都不会去伤害;猛禽和猛兽也不伤害刚生下的婴儿;刚生下的婴儿虽然筋骨柔弱但却能够紧握拳头。出生婴儿虽然不知道男女之间的事但却可以让阴部挺立,这是精气饱满的缘故;出生婴儿可以整天啼哭而不嗓音嘶哑,这是因为阴阳调和。身体上的精气(分阴阳)调和就称为平衡的常态,知道什么是常态和常理叫做明鉴。可以有益于事物生长的就称为祥。心神可以指引精气的就称为强(道家养生原理把人身体理的精、气、神看做是基本元素,神可以指引精、气沿经络行走聚合就可强身壮体)。事物发展到壮年就开始衰落的过程,这再道家的观念来说称为“不道”(不符合道的原理),不符合道的原理的就会早早衰亡。
本章要义:道家对于人的生长过程研究透彻,连现代才有所注意的儿科,再古代就已经很有研究,对于毒蛇猛禽猛兽不伤害婴儿,我们现代人也只能从古代的文献中才可以知道。用婴儿不受伤害来比喻道德修养好的人也不受伤害,以此说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老子》第五十六章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了解道德修养和教化的人是不会用语言去教导别人遵守道德的(他们会以身作则用行动去教导人们遵从道德规则)。经常用语言去教导别人的人是不了解道德修养教化方法的。避免混淆,区分使用范围。去掉锐气;接触纷争;减少炫耀;与卑微者同甘苦,这是最大的同化,也是德性的要求。因此有道德的人是无私的,他们不会因为亲情而徇私;有道德的人可以获得众人的认可,因此他们不会因为别人的离间而疏远;有道德的人没有自己的私欲,因此难以用利益诱导来做坏事;有道德的人因为不与别争利,因此也不会遭受祸害;有道德的人顺乎自然,发展顺利,因此很容易就获得信任和任命;有道德的人没有什么大的缺点,因此人们不会看不起他们。这么说来道德修养是获得尊重和社会认可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本章要义:讲明道德修养和教化的基本方法。强调道德教化不是用言论来教育而是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感化。
《老子》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正:光明正大,公平、公正(由道德的原理引申出来)。 奇:出人意料的,令人难以预测的。事:形声。从史,之省声。史,掌管文书记录。甲骨文中与“吏”同字。本义:官职。
以公平正义治理国家,以奇谋巧计用兵,以没有官吏的组织形态(人民战争、人民运动)获取天下。我怎么知道事物会按这样的态势发展的?这是根据以下实力得出的结论。天下规定百姓不能做的事越多则人民越贫困;民间存在很多的武器则城邦和家庭之间就出现很多的争斗,因此会出现混乱无序的状态;民间如果有很多人学习各类投机取巧的方法就会出现很多相互欺骗、残害的事件;一个国家有很多的法令就会有很多的罪犯(美国为例)。因此圣人说:“我顺其自然的实行治理,则老百姓会自然归化,社会和谐;我喜好安定则老百姓自然的就会有公正平和的心态;我不用设置官吏而老百姓会自然的富足;我没有什么私欲则老百姓就会很淳朴。
本章要义:讲明获得与治理天下要点是与民同甘共苦,将百姓利益视同为自己的利益就可以顺利发展。
《老子》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治理的政令不经常有,好像不通畅,这样的状态下民风是淳朴的。治理的政令事无巨细都有规定,那么民风奸诈,缺失道德。“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韩非子》解老)祸福既然相倚,那谁又能够知道它们的界限是什么?怎么分辨?难道事物没有正邪之分吗?依照道德而来的公平正义可以转化表现为奸谋奇巧(美国利用市场经济原则掠夺全世界);帮助人的善事可以转变为害人的事情(劝学生学习导致学生自杀),这些都是人世间的迷惑。这样的迷惑已经由来已久也。(很多人本来的人生目标是为了长寿,为了富贵,但所作所为又与人生目标相异。这是过分相信有捷径而走上邪路)因此圣人的行为是:处在领导地位不会分别对待部下和事物,会一视同仁;处在辅助地位则不会随便去中伤诋毁别人;可以谦虚直率的发表各种建议和意见,但不会放肆的得罪别人;有功劳和成绩不会过分的炫耀,而会让参与者共同分享荣耀。
本章要义:“祸福相倚”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里面包含着这样的哲学观念“量变道质变”,因此中国人“过犹不及”。
《道德经》注解(17)
《老子》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啬:会意。甲骨文字形,象粮食收入谷仓形。小篆从来回
|
|
,“来”是小麦,“回”(lǐng)是仓库。本义:收获谷物。中国字很玄妙,啬本身就是一来回,就是一个过程。因此老子的“夫唯啬”很有禅宗味道。这里指农业。
治理人民,按天理行事,最好就是搞好农业(需要按天时耕作,人民温饱)。如果重视农业则是按天理行事(服从道德,人民温饱,社会安定。就是“早服”)按天理行事就是重视积德,重视积德则战无不克(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韩非子解老》)。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则别人不知道能力的极限。别人不知道能力的极限则可以有余力来建立国家。建立国家的依据(重视农业),持续执行这样的政策,国家就可以保持长久。深其根,固其柢(树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禄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于理者,其持禄也久,故曰:“深其根。”体其道者,其生日长,故曰:“固其柢。”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韩非子解老》),这是长久生长的持续之道,这可以看作是“道”贯彻。
本章要义:农耕社会以农业为主,老子强调重视农业是因为农业要按照四季变化来耕作,而且农业是解决温饱的根本。即使再现代社会农业也是根本。重视农业就是按“道”的原理办事。坚持这样的原则就可以建国,而且建国后国家可以持久。
《老子》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治理大国的原则应该象烹煎小鱼一样不要轻易翻动更改(有烹饪经验的人就知道,烹煎小鱼如果常翻动则小鱼会碎成一团)。用“道”的原理来治理天下,则那些鬼怪都不灵验了。不是鬼怪没能力,而是鬼怪不再伤人。不但鬼怪不伤人,圣人也不会伤人(不使用刑罚)。这样鬼怪和圣人都不伤人,就是积德和谐的社会。
本章要义:治国的原理就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能随意更改,随意更改,人民难以适从,社会就会发生动乱。很恰当的比喻。
《老子》第六十一章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以静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
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使天下百川河流在这里交汇。大国要处在天下雌柔的位置,雌柔常以安静守定而胜过雄强,这是因为雌性的特点是静和下(意指宽容接纳)。大的国家以礼下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小国家,则会令小的国家听从号令或归顺。小的国家以弱小谦卑的姿态与大国打交道,则可以从大国方面获得自己需要的帮助。有些是用礼下谦卑的态度获得帮助,有些用宽容接纳的姿态获得认同。因此,大国不能有过分的欲望,还要具有宽容、帮助别人的心态。小的国家也一样不能有太高的欲望,可以以谦卑的心态听从大国的建议。这样大国和小国都得到欲望上的满足,因此为领导者都要礼下,用宽容的态度行事。
本章要义:这是中国最早的国际关系论述。国际关系的相处要点是互相尊重,要礼下,要宽容,不能有太多的要求和欲望。
《老子》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葆也,不善人之所葆也。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何:古同“呵”,谴责。
“道”贯穿于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道”善良的人珍惜它,不善良的人也需要“道”庇护。美好的言辞可获得尊重,美好的行动可帮助人,会获得人们的赞赏,进而获得信任。人的不良言行,要责问怎么让它们存在?因此刚就任的天子或三公,虽然有玉器和马车这样优越的生活享受也要坚持培养美好的言辞和行动。古代人提倡要有美好言辞,有良好的行为,为什么?(美好的言辞和良好的行为是自己的修养,初始并没有获得回报的要求,但却有好的回报。)不提倡获得和回报(提倡公德),因为有获得回报的心态办事就要犯罪,就要偏斜。因此有美好言行的人可以尊贵于天下。
本章要义:讲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美好的言辞和良好的行为是获得社会认可的最好路径。
《道德经》注解(18)
《老子》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抱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事:形声。从史
|
|
,之省声。史,掌管文书记录。甲骨文中与“吏”同字。本义:官职。
做事的方法是从事物演变发展的初始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行政管理的方法就是精简官吏,最好是回归到那种没有官吏的治理状态。饮食烹饪的最高境界就就是呈现原始纯真的味道。大小、多少、抱怨、以德这些相对立的概念都是没有绝对的它们是相对得出来的。要确定它们的定义很难吗?其实也不难。要做大事、大器吗,那么必然都要从小处做起。天下所有的难事都是从简单容易的事开始。天下的大建筑物,都是从基础和小部件做起。因此,圣人不考虑做大的事,他们已胸有成竹,考虑的只是那些局部怎么完成。因此圣人做大事可以成功。那些轻易许诺的必然没有什么信誉(随意许诺难以践行),因此很多有信誉的人并不会随便的给人许诺。就是因为这样圣人对别人的要求好像都很难答应,但是我们要求圣人做到的事好像最终还是给办成了。
本章要义:讲明大事由小处做起的道理。如果人要有信誉就不要随便许诺。
《老子》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pàn),其微易散。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恒于几成而败之。故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中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也。
局面安定的情况容易维持,在没有发生变乱的时候,做规划就很容易。事物脆弱时容易消解;事物细微时容易散失。处理事情要在事情未发生时就做好准备(预案),行政治理要在没有发生动乱之前就先现出动乱的根源。合抱粗的树木都是由枝桠细苗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也是从一点点的细土夯合而成。到达千里之外的地方,也必须一步一步的从出发的地方开始。有所作为的将会招致失败,有所执着的将会遭受损害。因此圣人无所作为,所以也不会招致失败,无所执着所以也不遭受损害。人们做事总是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失败。因此我们做事要从开始到结束以致保持谨慎,以免因不小心而失败。因此圣人想的是一般人没想到的事情;圣人治理之道就是不将稀缺物资的价格抬高。圣人学习不学那些没用的知识,而是抓住要点解决主要矛盾,它们不会重复平常人的错误。并且用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来辅助处理事物。一切都顺其自然,不敢照自己的意愿而拂逆自然规则。
本章要义:做事要从小做起,做事要善始善终。
《老子》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知治国国之贼;不以知治国国之德。知此两者,亦稽式。恒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
古代善于运用“道”的圣人,他们不是将“道”的原理讲解给民众明白,而是以行动教育,让民众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才正确。民众对于“道”的原理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了解。人民知所以哪一治理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拥有很多投机取巧的知识。因此用智谋奸巧来治理国家,最终会祸害国家(上行下效,投机取巧之风盛行,则国家的生产能力下降,反受其害。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切顺其自然的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气,因为顺其自然,民风淳朴,生产稳定。则不管发生什么样大的变故都可黯然度过(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就是这样)。要知道“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是衡量是否按道德原理办事的定式。知道治理国家的定式,按照道德原理来治理就是最好的“德性”。德性积累深了、时间长了,则会到达与原来事物发展相符合的状态,这样己可以做什么事都顺利。
本章要义:“以智治国,国之贼”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根本原理。国家治理如果以巧智机谋获取利益,则民众会效法。民众多奸谋则社会混乱,社会混乱则国家不稳。本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使用权谋,结果民众跟随学习使用奸谋则社会乱,这就会导致国家溃散。其结果是祸害国家,很多统治者并不知道这样的原理。美国现在就是受使用奸诈权谋的危害。
《老子》第六十六章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天下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
江海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河流所汇往的地方,乃是由于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方,所以能够成为百川之王。因此,圣人要领导人民,必须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所以,有道的圣人虽然地位居于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负担沉重;虽然领导统治人民,而人民并不会怨恨加害。而且天下的百姓都会乐于推举他们成为领导者,一点都不会厌恶。这不就是与人无争而自然得到的实例吗?圣人不与民争利,因此天下人都不能够与他竞争。
本章要义: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是圣人之道。“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表现。毛泽东现代圣人也。
《道德经》注解(19)
《老子》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不病。
知道自己的知识有限,不骄傲,可以虚心待人接物是最好的习惯。自以为是,不知道学习进步的人是有毛病的。就是因为担心自己有毛病才不会轻易生病。
|
|
圣人没有毛病,是因为厌恶自满,会时刻检讨自己的不对进行纠正,因此我们看起来圣人是没有毛病的。
本章要义:知识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我们在遇到事情时可以通过学习来了解新鲜事物。切忌自满,要虚心。
《老子》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弗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彼而取此。
人民不畏惧权威,则是法律公平、社会秩序良好的具体表现,这样的权威体现在大处。不要轻侮自己居住的地方(要弄干净,要尊重,这是养生的要求。日本就受道德经影响很注重居住地的整洁)。不要讨厌自己的生活,不管自己处于什么境地好而地位都不要心生厌烦,只有顺其自然才能适应环境(这也是道德经要求的养生原理,不抱怨才能有好心情,才能长寿)。因为不厌弃自己的居住地,也不厌弃自己的生活,这样才能够适应环境,才不会遭受社会和环境的唾弃。这是生存之道!因此圣人知道自己再什么时候过什么样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事。他们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生活态度,不会因为过于看重自己而不适应社会。圣人爱惜自己的才能和身体,但圣人不会讲自己看得很高贵,会适应形势。因此道的要求是顺其自然,要适应环境而不是与环境作对。
本章要义:“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是道德经重要的养生原理。照这样的原理生活,己可自然的改变自己的运气。也可乐观长寿。
《老子》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勇于果敢做事的人会因为失去谦逊退让而遭致祸害,因此会找来杀生之祸。勇气不足者,因为有所限制,遵守法律而不会遭受法律的惩罚,因此可安生长寿。敢与不敢因为态度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有害的。天理(道)所厌恶的,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天理是不用争斗而可以轻松获胜;不用言语而能够轻松应变;不用召唤而可以使需要的人或物临近;光明坦荡而有谋略。天理象渔网一样笼罩整个世界,看起来有很多大的孔隙,但天理报应是没有遗漏的。
本章要义:要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原则,逞勇斗狠,与人相争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大的好处。世界的规则象物力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要谨慎使用外力破坏环境和发展过程,否则讲遭受客观发展规律的惩罚。
《老子》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恒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恒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zhuó)。夫代大匠斲者,则希不伤其手矣。
人民不畏惧死亡(生活艰难,生无可恋,因此不怕死),为什么用死来吓唬他们呢?假使生活安定,那么人民都有生存的意愿,则他们就会很怕死。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作奸犯科的人出现,那么即使有通缉令或诛杀令,谁还敢自己去杀这样的犯人?因为有政府和法律等候着。平常的制度理就有专门惩罚诛杀犯罪者的人来维护秩序。假如统治者想用自己的意愿来代替制度执行惩罚诛杀,则好像是使用不熟悉工具的人来代替木匠来进行砍伐木头的工作,那些不熟练的人代替木匠进行砍伐工作的人很少有不上到手的。
本章要义:强调刑罚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社会要安定需要有公平的法律和正常的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是维护生活秩序的根本。
《道德经》注解(20)
《老子》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民之轻死者,以其上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也。
天下的民众之所以遭受饥饿,是因为统治者的赋税太多的缘故。因为饥饿人民就
|
|
很难治理。饥饿的人民难治的原因是因为统治者不量力而行,多花费导致的。人民之所以轻生冒死,是因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奢侈生活,过度向人民征税。人民生活艰难自然就无所谓生死了。只有那些不过分注重自己养生的统治者,才能够顺利养生,他们比那些过分注重养生者聪明。因为过分养生会造成人民贫困,贫困则会造反动乱,造反动乱则会令统治者不能有正常的寿命。
《老子》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死了以后身体就变得僵硬。草木生长时是柔软脆弱的,死了以后就变得干硬枯槁了。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柔弱的东西属于生长的一类。因此,用兵逞强就会遭到灭亡,树木强大了就会遭到砍伐摧折。凡是强大的,总是处于下位,凡是柔弱的,反而居于上位。
本章要义:指出柔弱是生长、长寿的要诀,人不能够到处逞强。处事这样不逞强,身体锻炼也一样不能过分强壮。
《老子》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yú)?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之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损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张:形声。从弓,长声。本义:把弦安在弓上。
自然的规律是不是如制作弓箭一样?将高翘起的部位压平或削平,不足或低下的部位进行垫高或辅加垫板加强,这样力量平衡,劲道足才可组成射箭的弓。有多余的要减少,不足者要补足,制作弓箭的原理就象天理一样。自然运行的原理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际社会的运行规律则相反那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什么人可以执行损余而补足天下的?唯有得道的圣人。因此圣人行事看起来象没有做什么事,领导促成某些事的发展,但却不居功。象圣人这样的行事方式就是:不想树立榜样啊(不尚贤)。
本章要义:“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自然界的运行原则。按自然行事才可长久。
《老子》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故圣人之言云:受国之詬,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之王。正言若反。
遍天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而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胜过水。弱胜过强,柔胜过刚,遍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实行。因此圣人说:能够代表人民承担全国耻辱的就可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现代的原始社会研究报告中,就有部族头领要成为头领的仪式就是接受全族人啐唾);可以代表人民承担国家灾祸的人就可以成为国家的君王。正确的话,我们听起来却好像不现实一样。
本章要义:“以柔克刚”是中国人独有的世界观,也可以说这观念来源于《老子》。
《道德经》注解(21)
《老子》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馀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
和解大的冤仇,必然会剩余一些小的冤仇(一样会有仇视)。但不是说仇怨就没办法消除。消除仇怨的唯一办法就是与人为
|
|
善,不积仇怨。仇怨一旦积累就很难消除。因此圣人以光明睁大的契约(法律)来约束民众的行为(一视同仁,没有亲疏贵贱),而不是用法律的惩罚民众,让统治者逃避责罚。因此有德的执政法律象契约一样,而没有德的法律则只是一种责罚民众的刑罚(有亲疏贵贱之分,不公平)。天道要求是没有亲疏的,而且天道也要求要经常的帮助别人。
本章要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论及法的精神的文字,比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要早两千多年。
《老子》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的国家人民少,即使有很多种类的高级武器他们一而不会使用。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扩张的欲望和能力。因此治理国家是减少人民的欲望,让人民的生活安定,珍惜生命。有安定的生活后,人民就不愿意迁徙道远处了。即使有船和马车,人民都不用,因为安居乐业并不需要到别处讨生活(知限于古代,现代就有生命旅游的说法了);虽然国家有穿铠甲的士兵,但国家内外和谐,根本不需要使用甲兵。这样就可以回复到以前原始社会结绳记事时那样淳朴的民风,这就是最好的治理------人民各自享受着甘美的饮食;各自享受鲜美的衣服;各按自己的风俗习惯生活;大家安居乐业。因为国家小,临近国家的人民可以相互望见,鸡鸣狗叫之声相互间可以听见,但是因为生活安定大家不相侵害,到死都不会相互来往。(这是老子关于理想国家和生活的设想,有点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乌托邦)
本章要义:老子的理想注意思想在现在虽然不适应,但确是老子回归淳朴思想的具体表现。这有点象卢梭说的私有制就是各种生活恶习的开端,但伏尔泰一样回信说希望过私有制有恶习的生活(宁愿两条腿走路),而不愿回归到原始人状态。这就是现实。
《老子》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真实可信的话不漂亮,好听舒服的话不中用。善良者不会去狡辩,狡辩着不善良。真正有知识的人不卖弄,经常卖弄自己知识的人实际上水平有限。圣人为人处事是没有积累的,他所有的财富都用来帮助别人了。自己越是财富越是用来帮助别人。因为老是帮助别人,也能获得别人帮助,因此就有很多赚钱和积攒财富的机会,因此“己愈多”。天理的原则是:帮助而不施加祸害。人际关系的原则是:做事不要相争。
本章要义:总结性言论,说明自己的理论虽然不怎么中听但实际。讲清天之道和人之道。为人们做事知名方向。
道与仁
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他们创立的道家和儒家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大学派,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对于这些思想,学界更多地是注意到了两者的差异,而对其统一性认识得并不深入。我们从道德和仁爱这两个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入手,看一看老子和孔子思想的统一性。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仁的涵义就是“爱人”(《论语·颜渊》),爱自己,爱他人都是“爱人”,但孔子主要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要互爱,你爱我,我爱你,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要全身心地去爱他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是一种极为高尚的道德境界。那么,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要克除自己意识中不符合仁爱要求的内容,按照礼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最终达到意识一动就是仁爱的状态。
道是老子思想的中心,也是中国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它的主要涵义是生养宇宙万物的母体,即宇宙万物的本源。道不仅产生万物,还养育万物,它是世间万物不断发展和繁盛的原动力,离开了道,世间万物就不能变化发展。世界万物,包括人、人类社会的生生不息、蓬勃向上的发展是道的一种表现。道生成涵养万物的本性就是德,正如庄子对“德”的解释:“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谓德。”(《庄子·天地》)庄子以“生”来解释“德”。道和德是宇宙最根本的物质及其最根本的性质,它们是体和用的关系,德是道的功能展现。《管子》也以“生”来解释德,《心术上》说:“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道以德的形式存在着,道的生长化育的本质是靠德来表现的。老子又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生成万物而又畜养、载育万物是道的功能,道生成畜养万物又不主宰它,不自以为功高而占有它,是自然而然的,这是“玄德”,是最大的德。老子的这种道德观是从宇宙自然来立论的,但它同样涵盖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念,因为人类社会也离不开道的德性。
老子的道德观是自然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统一。这就为他与孔子思想的统一性打下了理论基础。道的生长、畜养万物的生生不息的功能本性落实到人类社会,就是仁爱的大善德,仁爱就是让人人都好、人人都能成长、发展,这是道的大善德在社会中的体现,这是社会中人与人关系上的最大的“玄德”,即生生之德。它虽然属于社会道德的内容,但又深深根植于道的功能本性的自然道德之中,自然道德和社会道德在生之大德上是相通的,这就是老子和孔子思想统一性之根本。
在阐发仁爱是生生之德这一主题上,程朱有着十分形象的比喻。程伊川以植物种子的生长发育的功能为仁,他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又说:“心犹种焉,其生之德,是为仁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他把植物种子的生之性、生之德叫做仁,以生长发育的本性、德性喻仁,这与老子的道德生长化育万物的生之功能本性是一致的。朱熹也同样发挥仁的生生之德说,他说“如谷种,桃仁、杏仁之类,种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朱子语类》卷六)程伊川和朱熹都把仁解释为生之德,实际是把仁爱与道德以“生之德”统一了起来。朱熹在解释《道德经》的时候,认为程伊川的“生生之意”的思想取自老子。他在对学生解释老子的“谷神不死”一节时说:“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取老氏之说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他承认仁爱的“生生之意”说来自老子的道的生长之功能德性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与现代伦理学的道德观有很多不同点。现代伦理学主要内容是人与人相处的行为准则和义务等,而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则是包括人与自然、社会的秩序和规范的一个整体大系统,它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道德与仁爱的关系就是这种整体观的体现。我们来看“克己复礼为仁”的“礼”,它更接近于现代伦理学的道德规范的涵义。《礼记·礼运》说:“圣人所以治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七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十义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节、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就是规范人行为的准则,遵从这些准则以达到社会中人与人的和谐相处的目的。《礼记》认为这种人伦秩序规范的本源根植于宇宙大自然之中,即从根本上说礼来自于道。《礼运》说:“故礼者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这也与老子的观点一致。按照老子的观点,道产生了万物,也产生了人和人类社会,道是自然万物、人与人类社会的本根,道的德性就是生长化育的功能,人的生命、人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道的能生之德,所以,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行为规范,即现代伦理学的道德规范要以道的能生的德性为本根,这一点也为伦理学的诸内容所证明,伦理学的目标也在于建立一个有利于人与人相处,有利于人类和谐发展的社会。
孔子对道的生生之德是有深刻感受和认识的,他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并没有说什么话,但它却推动宇宙大自然的运行,它使万物生长繁育。这里的天就是天道,就是老子的生养万物之道。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生养自然万物,而人道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孔子正是把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把道落实到人间,以仁爱作为人间伦理道德法则的根本。
既然老子的道德和孔子的仁爱涵义相一致,那怎么解释老子的“绝仁弃义”呢?从老子“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这句话,我们知道老子在论述大道和仁义的关系上有个先后的顺序。老子的理想社会是大道倡行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用提倡什么仁义,人们都自然地遵从大道的要求,所想所做都符合道,提倡仁义反而是多余的。历史无情地发展使大道不再倡行,私欲、对物质的占有欲支配了人们的生活,这种社会现实就不得不提倡仁义,并按照礼的规范去做了,正如老子所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三十八章)当道德丧失,社会充满不仁不义的行为时,就要以礼来约束了。“当人类社会失去了道德的制衡能力而只能靠僵硬的礼来强人就范时,祸乱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老子评传》第217页)这样的礼,是社会动乱的开端,当然就是“乱之首”了。
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根,在当代社会,它也超越了国家、民族和宗教,无论是对于生态伦理,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都是具有建设性的。
(作者常大群单位: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宗教学研究所)
马王堆帛书版《道德经》(珍藏研读)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古书,其中就包括2170年前的古本《老子》(100年后被称为《道德经》)。结果经过整理复原,人们发现,该版本《老子》与我们现在流行的《道德经》版本,存在着一些差异。

《道德经》全文
马王堆出土帛书版
《史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至今有三个版本源头:一个是相传从河上公传下来,魏晋人王弼注释的版本,是现代通行本的祖宗。一个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甲乙两个版本,还有一个是郭店楚简中的《老子》残编。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有甲、乙两种版本。两版本的书体有些不同,但都属于隶书。乙本避刘邦讳,可以断定它是汉朝的抄写本无疑。甲本由于不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因此可推断它当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前。
过去多以为隶书出现在秦篆之后,是“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从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一千一百余枚隶书秦简和1980年又在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两件隶书战国木牍的情况来看,隶书的出现与流行应早于秦篆。现代大量考古发掘证明,隶书在战国时期就已广泛使用于以竹木为书写材料的简牍上。
甲本帛书很有可能是直接从战国时期的竹简上转抄过来的,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保存最为完整、最接近原貌的古本《老子》版本。三国时魏人王弼注《道德经》则是现存传世本中的最早版本。
帛书本不分篇章,传世本《老子》则分为上、下篇共八十一章。文字也多所不同。
以下是帛书《老子》甲乙本合校的简体字复原文本。
帛书《老子》甲、乙本合校及文字复原

德 经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皮(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霝(灵),浴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为正。其致之也,胃(谓)天毋已清将恐裂,胃(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胃(谓)神毋已霝(灵)将恐歇,胃(谓)浴(谷)毋已盈将将恐渴(竭),胃(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谓)曰孤寡不(谷),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致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
上士闻道,堇(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真如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褒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勿(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故人之所教,夕(亦)议而教人。故强良(梁)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父。
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致(至)坚。无有入于无间。五(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敝)。大盈若(冲),其用不(宭)。大直如诎(屈),大巧如拙,大赢如。趮(躁)胜寒,靓(静)胜炅(热)。请(清)靓(静),可以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
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歙) (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属耳目焉,圣人皆咳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辟矢(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矢(兕)无所椯(揣)其角,虎无所昔(措)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闷),闭其门,终身不堇(勤)。启其闷,济其事,终身不棘。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道〈遗〉身央(殃),是胃(谓)袭常。·
使我 (挈)有知也,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货财有余。是谓夸。夸,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逢(蜂)()(虺)地(蛇)弗螫,攫鸟猛兽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而朘怒,精之至也。终曰〈日〉号而不,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即老,胃(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闷,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坐(挫)其阅(锐),解其纷,是胃(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浅(贱)。故为天下贵。·
以正之(治)邦,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滋)昏。人多知(智),而何(奇)物兹(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其政闵闵,其邦屯屯。其正(政)察察,其邦夬(缺)夬(缺)。(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曜。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惟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胃(谓)深槿(根)固氐(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治大国若亨(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申(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交)也,牝恒以靓(静)胜牡。为其靓(静)也,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故大邦者宜为下。
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宝)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加)人。人之不善也,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善〈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胃(谓)求以得,有罪以免舆(与)?故为天下贵。·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未(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冬(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猷(犹)难之,故终于无难。·
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羸(蔂)土。百仁(仞)之高,台(始)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人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
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智)也。故以知(智)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智)知邦,邦之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此胃(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乐隼(推)而弗猒(厌)也,非以其无诤(争)与?故天下莫能与诤(争)。·
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送〈徙〉。有车周(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 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天下皆谓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宵(肖)。若宵(肖),细久矣。我恒有三葆(宝),之,一曰兹(慈),二曰检(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今舍其兹(慈),且勇;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兹(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女(如)以兹(慈)垣之。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胃(谓)不诤(争)之德,是胃(谓)用人,是胃(谓)天,古之极也。·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进寸而芮(退)尺。是胃(谓)行无行,襄(攘)无臂,执无兵,乃(扔)无敌矣。(祸)莫于〈大〉于无适(敌),无适(敌)斤(近)亡吾吾葆(宝)矣。故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褱(怀)玉。
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之不畏畏(威),则大威将至矣。· 母(毋)闸(狎)其所居,毋猒(厌)其所生。夫唯弗猒(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被(彼)取此。·
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栝(活)。知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若民恒是〈畏〉死,则而为者吾将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夫伐〈代〉司杀者杀,是伐〈代〉大匠斲也。夫伐〈代〉大匠斲者,则希不伤其手矣。·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巠(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巠(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仞贤(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细,生之徒也。”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恒。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
天下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印(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惟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也。故圣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诟),是胃(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胃(谓)天下之王。正言若反。
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右介(契)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介(契),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

道 经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有(又)玄,众眇(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意〈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隋(随),恒也。是以声(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是以弗去。
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声(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潚(渊)呵始(似)万物之宗。锉(挫)其,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或存。吾不知谁子也,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圣)人不仁,以百省(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钥舆(与)?虚而不淈(屈),踵(动)而俞(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浴(谷)神不死,是胃(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胃(谓)天地之根。绵绵呵若存,用之不堇(勤)。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声(圣)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舆(与)?故能成其私。
上善治(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争),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潚(渊),予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静(争),故无尤。
(殖)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之,可长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述(遂)身芮(退),天之道也。
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抟气至柔,能婴儿乎?修(涤)除玄蓝(鉴),能毋疵乎?爱民活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为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是谓玄德。
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然(埏)埴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五色使人目明〈盲〉,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声(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罢(彼)耳〈取〉此。
龙(宠)辱若惊,贵大梡(患)若身。苛(何)胃(谓)龙(宠)辱若惊?龙(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胃(谓)龙(宠)辱若惊。何胃(谓)贵大梡(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梡(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梡(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何〈可〉以寄天下。
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计(诘),故而为一。一者,其上不,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胃(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谓)道纪。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达,深不可志(识)。夫唯不可志(识),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涉水,犹呵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客,涣呵其若凌(凌)泽(释),呵其若(朴),湷呵其若浊,呵其若浴(谷)。浊而情(静)之,余(徐)清。女〈安〉以重(动)之,余(徐)生。葆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至虚极也,守情(静)表也。万物旁(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曰静。情(静),是胃(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沕(没)身不怠。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案(安)有不信。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省(姓)胃(谓)我自然。
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智)快(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畜(孝)兹(慈)。邦家(昏)乱,案有贞臣。
绝声(圣)弃知(智),民利百负(倍)。绝仁弃义,民复畜(孝)兹(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唯与诃,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恍呵其未央哉!众人(熙)(熙),若乡(飨)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佻(兆),若婴儿未咳。累呵如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遗。我禺(愚)人之心也,蠢蠢呵。鬻(俗)人昭昭,我独若(昏)呵。鬻(俗)人蔡(察)蔡(察),我独(闷)(闷)呵。忽呵其若海,望(恍)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悝(俚)。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忽。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望(恍)呵忽呵,中有物呵。(幽)呵呜(冥)呵,中有请(精)〈呵〉。其请(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以此,
炊者不立,自视(示)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
曲则全,枉则定(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声(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自视(示)故明,不自见故章,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全者几语才(哉),诚金(全)归之。
希言自然。飘风不冬(终)朝,暴雨不冬(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得)者同于德(得),者〈失〉者同于失。同德(得)者,道亦德(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绣(寂)呵缪(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远,远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为巠(轻)根,清(静)为趮(躁)君。是以君子众(终)日行,不离其甾(辎)重,唯(虽)有环官,燕处则昭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巠(轻)于天下?巠(轻)则失本,趮(躁)则失君。
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适(谪),善数者不以梼(筹)(策)。善闭者无(关)龠()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 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声(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胃(谓)明。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赍(资)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赍(资),唯(虽)知(智)乎大眯(迷)。是胃(谓)眇(妙)要。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鸡〈离〉。恒〈德〉不鸡〈离〉,复归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恒德乃足。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貣(忒)。德不貣(忒),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物或行或随,或炅(热)或吹,或强或挫,或坏(培)或撱(堕)。是以声(圣)人去甚,去大,去楮(奢)。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朸(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铦袭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便(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依(哀)立(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恒无名,(朴)唯(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谷〈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浴(谷)之与江海也。
知人者,知(智)也。自知者,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忘者,寿也。
道泛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声(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饵,过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谈(淡)呵其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
将欲拾(翕)之,必古(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古(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谓)微明。友弱胜强,鱼不脱于潚(渊),邦利器不可以视(示)人。
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情(静),天地将自正。

【附录·原文】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释文
【甲本《德经》】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皮(彼)取此。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霝(灵),浴【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为正。其致之也,胃(谓)天毋已清将恐【裂】,胃(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胃(谓)神毋已霝(灵)【将】恐歇,胃(谓)浴(谷)毋已盈将将恐渴(竭),胃(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谓)【曰】孤寡不(谷),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致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上士闻道,堇(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真如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褒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勿(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故人【之所教,】夕(亦)议而教人。故强良(梁)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父。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致(至)坚。无有入于无间。五(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敝)。大盈若(冲),其用不(宭)。大直如诎(屈),大巧如拙,大赢如。趮(躁)胜寒,靓(静)胜炅(热)。请(清)靓(静),可以为天下正。·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属耳目焉,圣人皆【咳之。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辟】矢(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矢(兕)无所椯(揣)其角,虎无所昔(措)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闷),闭其门,终身不堇(勤)。启其闷,济其事,终身【不棘。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道〈遗〉身央(殃),是胃(谓)袭常。·使我 (挈)有知也,【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货【财有余。是谓夸。夸,非道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逢(蜂)()(虺)地(蛇)弗螫,攫鸟猛兽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而朘怒,】精【之】至也。终曰〈日〉号而不,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即老,胃(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闷,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坐(挫)其阅(锐),解其纷,是胃(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浅(贱)。故为天下贵。·以正之(治)邦,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滋)昏。人多知(智),而何(奇)物兹(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
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其政闵闵,其邦屯屯。】其正(政)察察,其邦夬(缺)夬(缺)。(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曜。治人事天,莫若啬。夫惟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胃(谓)深槿(根)固氐(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治大国若亨(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申(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交)也,牝恒以靓(静)胜牡。为其靓(静)【也,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故大邦者宜】为下。【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宝)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加)人。人之不善也,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善〈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胃(谓)求【以】得,有罪以免舆(与)?故为天下贵。·为无为,事无事,味无未(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冬(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猷(犹)难之,故终于无难。·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羸(蔂)土。百仁(仞)之高,台(始)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人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智)也。故以知(智)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智)知邦,【邦之】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此胃(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江】海之所以能为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乐隼(推)而弗猒(厌)也,非以其无诤(争)与?故【天下莫能与】诤(争)。·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送〈徙〉。有车周(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天下皆谓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宵(肖)。若宵(肖),细久矣。我恒有三葆(宝),之,一曰兹(慈),二曰检(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今舍其兹(慈),且勇;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兹(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女(如)以兹(慈)垣之。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胃(谓)不诤(争)之德,是胃(谓)用人,是胃(谓)天,古之极也。·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进寸而芮(退)尺。是胃(谓)行无行,襄(攘)无臂,执无兵,乃(扔)无敌矣。(祸)莫于〈大〉于无适(敌),无适(敌)斤(近)亡吾吾葆(宝)矣。故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褱(怀)玉。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民之不】畏畏(威),则【大威将至】矣。·母(毋)闸(狎)其所居,毋猒(厌)其所生。夫唯弗猒(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被(彼)取此。·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栝(活)。【知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若民恒是〈畏〉死,则而为者吾将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夫伐〈代〉司杀者杀,是伐〈代〉大匠斲也。夫伐〈代〉大匠斲者,则【希】不伤其手矣。·人之饥也,以其取食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 民之巠(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巠(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仞贤(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细,生之徒也。”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恒。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天下【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印(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惟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也。故圣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诟),是胃(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胃(谓)天下之王。【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右介(契)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介(契),【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
【甲本道经】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有(又)玄,众眇(妙)之【门】。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意〈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隋(随),恒也。是以声(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是以弗去。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声(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潚(渊)呵始(似)万物之宗。锉(挫)其,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或存。吾不知【谁】子也,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圣)人不仁,以百省(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钥舆(与)?虚而不淈(屈),踵(动)而俞(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浴(谷)神【不】死,是胃(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胃(谓)【天】地之根。绵绵呵若存,用之不堇(勤)。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声(圣)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舆(与)?故能成其私。上善治(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争),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潚(渊),予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静(争),故无尤。(殖)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之□,□可长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述(遂)身芮(退),天【之道也。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抟气至柔,】能婴儿乎?修(涤)除玄蓝(鉴),能毋疵乎?爱【民活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为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是谓玄】德。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然(埏)埴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五色使人目明〈盲〉,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声(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罢(彼)耳〈取〉此。龙(宠)辱若惊,贵大梡(患)若身。苛(何)胃(谓)龙(宠)辱若惊?龙(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胃(谓)龙(宠)辱若惊。何胃(谓)贵大梡(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梡(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梡(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何〈可〉以寄天下。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计(诘),故【而为一。】一者,其上不,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胃(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谓)【道纪。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达,】深不可志(识)。夫唯不可志(识),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涉水,犹呵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客,涣呵其若凌(凌)泽(释),□呵其若(朴),湷【呵其若浊,呵其】若浴(谷)。浊而情(静)之,余(徐)清。女〈安〉以重(动)之,余(徐)生。葆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至虚极也,守情(静)表也。万物旁(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曰静。】情(静),是胃(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沕(没)身不怠。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案(安)有不信。【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省(姓)胃(谓)我自然。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智)快(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畜(孝)兹(慈)。邦家(昏)乱,案有贞臣。绝声(圣)弃知(智),民利百负(倍)。绝仁弃义,民复畜(孝)兹(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唯与诃,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恍呵其未央哉!】众人(熙)(熙),若乡(飨)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佻(兆),若【婴儿未咳。】累呵如【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遗。我禺(愚)人之心也,蠢蠢呵。鬻(俗)【人昭昭,我独若】(昏)呵。鬻(俗)人蔡(察)蔡(察),我独(闷)(闷)呵。忽呵其若【海,】望(恍)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悝(俚)。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忽。【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望(恍)呵忽呵,中有物呵。(幽)呵呜(冥)呵,中有请(精)〈呵〉。其请(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以此,炊者不立,自视(示)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曲则全,枉则定(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声(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自】视(示)故明,不自见故章,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全者几】语才(哉),诚金(全)归之。希言自然。飘风不冬(终)朝,暴雨不冬(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得)者同于德(得),者〈失〉者同于失。同德(得)【者】,道亦德(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绣(寂)呵缪(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远,远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为巠(轻)根,清(静)为趮(躁)君。是以君子众(终)日行,不离其甾(辎)重,唯(虽)有环官,燕处【则昭】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巠(轻)于天下?巠(轻)则失本,趮(躁)则失君。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适(谪),善数者不以梼(筹)(策)。善闭者无(关)龠()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 】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声(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胃(谓)明。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赍(资)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赍(资),唯(虽)知(智)乎大眯(迷)。是胃(谓)眇(妙)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鸡〈离〉。恒〈德〉不鸡〈离〉,复归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恒德乃【足。】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貣(忒)。德不貣(忒),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物或行或随,或炅(热)或【吹,或强或挫,】或坏(培)或撱(堕)。是以声(圣)人去甚,去大,去楮(奢)。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朸(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铦袭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便(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依(哀)立(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恒无名,(朴)唯(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谷〈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浴(谷)之与江海也。知人者,知(智)也。自知【者,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忘者,寿也。道泛【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声(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饵,过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谈(淡)呵其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将欲拾(翕)之,必古(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古(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谓)微明。友弱胜强,鱼不脱于潚(渊),邦利器不可以视(示)人。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情(静),天地将自正。
【乙本德经】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德。上德为而以为也。上仁为之而以为也,上德〈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句(后)仁,失仁而句(后)义,失义而句(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泊(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罢(彼)而取此。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霝(灵),浴(谷)得一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至也,胃(谓)天毋已清将恐莲(裂),地毋已宁将恐发,神毋已灵将恐歇,谷毋已盈将渴(竭),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谓)孤寡不(谷),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至数舆舆。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上士闻道,堇(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德如浴(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真如渝,大方禺(隅),大器免(晚)成,大音希声,天〈大〉象刑(形),道褒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人之所亚(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称也。物或益之而云(损),云(损)之而益。人之所教,亦议而教人。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学父。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出于有,入于间。吾是以知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成如缺,其用不敝。大盈如冲,其用不穷。大直如诎,大辩如讷,大巧如拙,大赢如绌。趮(躁)朕(胜)寒,静胜热。知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天下有道,走马以粪。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云(损),云(损)之有(又)云(损),以至于为,为而不为矣。将欲取天下,恒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圣人恒心,以百省(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得)信也。(圣)人之在天下也欱(歙)欱(歙)焉,为天下浑心,百生(姓)皆注其耳目焉,圣人皆咳之。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又(有)三,而民生生,僮(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辟(避)兕虎,入军不被兵革。兕所椯其角,虎所措其蚤(爪),兵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死地焉。道生之,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胃(谓)玄德。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佁(殆)。塞其,闭其门,冬(终)身不堇(勤)。启其,齐其事,终身不棘。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遗身央(殃),是胃(谓)袭常。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他(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朝甚除,田甚,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猒(厌)食而赍(资)财有余,是谓□。□,非道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甚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夆(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哉)?以此。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々Γǚ洌荩玻┏妫常┥吒ズ眨В菽衩希停┦薷ゲ叮ú墙钊跞岫展獭N粗蚰抵岫鴸K怒,精之至也。冬(终)日号而不嚘,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锉(挫)其兑(锐)而解其纷,是胃(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也,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以正之(治)国,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国家滋昏。人多智能,而奇物滋起。法物兹(滋)章,而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其正(政)(闵)(闵),其民屯屯。其正(政)察察,其民缺缺。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兼(廉)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眺(耀)。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蚤(早)服。蚤(早)服是胃(谓)重积德。重积德则不克,不克则莫知其极。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胃(谓)深根固氐(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治大国若亨(烹)小鲜。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朕(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也。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国者不过欲并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宝)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乡〈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胃(谓)求以得,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为为,事事,味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若(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难。其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谋,其脆也易判,其微也易散。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合抱之木,作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蔂)土。百千之高,始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为也,故败也;执也,故失也。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曰:『慎冬(终)若始,则败事矣。』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知(智)也。故以知(智)知国,国之贼也;以不知(智)知国,国之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是胃(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也,乃至大顺。江海所以能为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是以能为百浴(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皆乐谁(推)而弗猒(厌)也,不以其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小国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远徙,又(有)周(舟)车所乘之,有甲兵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圣)人积,既以为人,己俞(愈)有;既以予人矣,己俞(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天下皆胃(谓)我大,大而不宵(肖)。夫唯不宵(肖),故能大。若宵(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恒有三(宝),市(持)而(宝)之,一曰兹(兹),二曰检(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兹(慈),故能勇;检(俭),敢〈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今舍其兹(慈),且勇;舍其检(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死矣。夫兹(慈),以单(战)则朕(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如以兹(慈)垣之。故善为士者不武,善单(战)者不怒,善朕(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胃(谓)不争之德。是胃(谓)用人,是胃(谓)肥(配)天,古之极也。用兵又(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胃(谓)行行,攘臂,执兵,乃(扔)敌。祸莫大于敌。敌近◎亡吾(宝)矣。故抗兵相若,而依(哀)者朕(胜)矣。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夫言又(有)宗,事又(有)君。夫唯知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褱(怀)玉。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民之不畏畏(威),则大畏(威)将至矣。毋(狎)其所居,毋猒(厌)其所生。夫唯弗猒(厌),是以不猒(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罢(彼)而取此。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栝(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亚(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单(战)而善朕(胜),不言而善应,弗召而自来,单(坦)而善谋。天罔(网),疏而不失。若民恒且◎不畏死,若何以杀(惧)之也?使民恒且畏死,而为畸(奇)者吾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又(有)司杀者。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则希不伤其手。人之饥也,以其取食之多,是以饥。百生(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以生为者,是贤贵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信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椊(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则不朕(胜),木强则兢。故强大居下,柔弱居上。天之道,酉(犹)张弓也,高者印(抑)之,下者举之,有余(余)者云(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下之道,云(损)有余(余)而益不足;人之道,云(损)不足而奉又(有)余(余)。夫孰能又(有)余(余)而有以奉于天者,唯又(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又(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朕(胜)刚也,弱之朕(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是故(圣)人之言云,曰:受国之(诟),是胃(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胃(谓)天下之王。正言若反。禾(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芥(契)而不以责于人。故又(有)德司芥(契),德司(彻)。天道亲,常与善人。《德》三千一。

【乙本道经】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欲也,以观其妙;恒又(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又玄,众眇(妙)之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亚(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隋(随),恒也。是以(圣)人居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昔(作)而弗始,为而弗侍(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知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不治矣。道冲,而用之有(又)弗盈也。渊呵佁(似)万物之宗。锉(挫)其兑(锐),解其芬(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佁(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也,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猷(犹)橐钥舆(与)?虚而不淈(屈),动而俞(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浴(谷)神不死,是胃(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胃(谓)天地之根。呵其若存,用之不堇(勤)。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私舆(与)?故能成其私。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居众人之所亚(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尤。(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允之,不可长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槫(抟)气至柔,能婴儿乎?修(涤)除玄监(鉴),能毋有疵乎?爱民栝(活)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胃(谓)玄德。卅楅(辐)同一毂,当其有,车之用也。(埏)埴而为器,当其有,埴器之用也。鉴户牖,当其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之以为用。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仿(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弄(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胃(谓)弄(宠)辱若惊?弄(宠)之为下也,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胃(谓)弄(宠)辱若惊。何胃(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橐(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命(名)之曰希。◎之而弗得,命(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计(诘),故而为一。一者,其上不谬,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命(名)也,复归于物。是胃(谓)状之状,物之象。是胃(谓)沕(忽)望(恍)。隋(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谓)道纪。古之□为道者,微眇(妙)玄达,深不可志(识)。夫唯不可志(识),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涉水,猷(犹)呵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客,涣呵其若凌(凌)泽(释),沌呵其若朴,湷呵其若浊,呵其若浴(谷)。浊而静之,徐清。女〈安〉以重(动)之,徐生。葆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至虚极也,守静督也。万物旁(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曰静。静,是胃(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芒(妄),芒(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大上下知又(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猷(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谓)我自然。故大道废,安有仁义。知(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又(有)孝兹(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绝(圣)弃知(智),而民利百倍。绝仁弃义,而民复孝兹(慈)。绝巧弃利,贱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忧。唯与呵,其相去几何?美与亚(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恍)呵其未央才(哉)!众人(熙)(熙),若乡(飨)于大牢,而春登台。我博(泊)焉未垗(兆),若婴儿未咳。累呵佁(似)所归。众人皆又(有)余(余)。我愚人之心也,湷湷呵。鬻(俗)人昭昭,我独若(昏)呵。鬻(俗)人察察,我独闽(闵)闽(闵)呵,沕(忽)呵其若海,望(恍)呵若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门元(顽)以鄙。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沕(忽)。沕(忽)呵望(恍)呵,中又(有)象呵。望(恍)呵沕(忽)呵,中有物呵。幼(窈)呵冥呵,其中有请(精)呵。其请(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此。炊者不立。自视(示)者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
物或亚(恶)之,故有欲者弗居。曲则全,汪(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自视(示)故章,不自见也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胃(谓)曲全者几语才(哉),诚全归之。希言自然。(飘)风不冬(终)朝,暴雨不冬(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有(又)兄(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得)者同于德(得),失者同于失。同于德(得)者,道亦德(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萧(寂)呵漻(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远,远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为轻根,静为趮(躁)君。是以君子冬(终)日行,不远其甾(辎)重,虽有环官(馆),燕处则昭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于天下?轻则失本,趮(躁)则失君。善行者达,善言者瑕适(谪),善数者不用梼(筹)(策)。善◎闭者关钥()而不可启也,善结者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圣)人恒善(救)人,而弃人,物弃财,是胃(谓)曳()明。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也。不贵其,不爱其资,虽知(智)乎大迷。是胃(谓)眇(妙)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贷(忒)。恒德不贷(忒),复归于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割。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物或行或隋(随),或热,或,或陪(培)或堕。是以(圣)人去甚,去大,去诸(奢)。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毋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谓)果而强。物壮而老,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亚(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铦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而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哀立()之;战朕(胜)而以丧礼处之。道恒名,朴唯(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卑(譬)道之在天下也,猷(犹)小浴(谷)之与江海也。知人者,知(智)也。自知,明也。朕(胜)人者,有力也。自朕(胜)者,强也。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寿也。道,沨(泛)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命(名)于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饵,过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将欲(翕)之,必古(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古(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古(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谓)微明。柔弱朕(胜)强。鱼不可说(脱)于渊,国利器不可以示人。道恒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阗(镇)之以名之朴。阗(镇)之以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道》二千四百廿六。